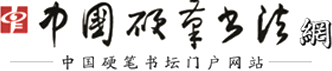我是随南下的父母在云南、四川长大的。我清楚的记得上幼儿园时就喜欢写写画画,为此还惹了不小的麻烦。那是在妈妈上班的办公楼里,放着几支氧气瓶,我便把它当作敌人的炮弹,随手在上面画了青天白日徽,这下可引起了当地公安、保卫部门的恐慌, 以为台湾特务在大陆搞策反宣传,便暗中调查,没有迹象,才怀疑是孩子所为,问到了我,我还很自豪地承认了。此事使得当地的领导虚惊了一场,六岁的我立即被保卫干部找去教导了一番,母亲也因对子女教育不严挨了批评,便把我送到部队,由父亲对我严加管教,可战士们却喜欢我在部队大院里随处留下的大炮、汽车、机关枪、红五星、红军旗等图画,还夸我画的好,画得象,说将来一定能成大画家,我当时心里想,画画是女孩作的事,才不当画家呢,男孩要当解放军,当大官。到了上小学,让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个生字写一排的语文作业,记得有一年暑假即将结束,母亲检查暑假作业时发现每天一页的毛笔大字竟一页也没写,便把我关在她的办公室里“反省”,我便从书包里找出一支破毛笔,蘸着办公桌上的蓝墨水三下二下完成了这份作业,母亲见后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带着我向老师求情,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却表扬我字写的不错,说是不象孩子写的字,当时我并没在乎老师的表扬,只是暗中庆幸终于混过了这一关。这些记忆最深的事,今天回想起来,都与书法有“嫌疑”,这是否就是我今天热爱书法的“潜伏期”不得而知。
到重庆上中学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虽成绩平平,但写得一手好字,的确让老师和同学都羡慕不已,学校抄大字报,办墙报都少不了我。有一次,我帮同学抄写的大字报贴出去不久,校方立即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的后台,事后才得知,校方分析大字报的字是成人所写而怀疑有幕后。高中临毕业前,语文老师将我写的两张毛笔字送到市里参加了中学生美术作品展,更使我沾沾自喜。在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也是这一手好字,不知使我躲过了多少次又累又脏的体力劳动,当地的贫下中农即羡慕又妒嫉。十九岁那年“开后门”当了兵,又是这手好字,第二年就当了文书,又借调到部队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免去了在基层连队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回到地方后,结识了当地一些书家,正赶上全国书法热,跑了许多地方,看了很多展览,开阔了眼界,方知一手好字与书法艺术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内在联系,从这时起,才真正走上研习书法艺术的道路。
在对前人书法的学习上,我和大多数学书者一样,颜楷打基础,二王、宋四家以及明清诸家作为行书学习的主脉,但更关注近、现代有成就书家书作,从中提取成功的信息。在,临习古人的作品上,我从来不敢把它们学的太深,太真,那样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这并不妨碍我对古代优秀法帖的广泛吸吮,但决不过多的留念,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一旦有了新的感受,就立刻记录下来。因此,我大都采用临摹—创作—临摹这种模式,力争使每幅作品都有新的面目。我以为,学书如登山,永远作攀登者,不要上到山顶,到了顶峰则意味着艺术生命的完结。攀登的感觉最好。
至于篆刻,我是从一角四分钱一本的《怎样刻印章》的小册子入门的,先学会基本的刀法,又临了些前人的印,平时多看各类印谱,有感而作,用铅笔在石面上大致画上印文,边刻边改,随刀随石应变,反复修改、制作,享受其中乐趣,我刻的印满意者不多,大都自用,故从不敢轻易为他人治印。
以上自白,仅供参考。尤其初学者切不可生搬硬套,以免贻误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