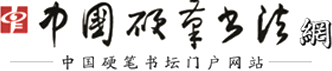书法:“半求王字半求官” ● 萧晴初 新青年论坛网站2003年5月30日发表了余杰先生的《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一文。人民网2003年6月06日网友李启咏的争鸣文章《书法是“文化摇头丸”吗?——和余杰先生商榷》。回应速度之快,是以前不多见的,可见网络的传播速度下信息共享的好处,人们足不出户即可阅读到最新的文章;以下分别简称为余文、李文。我要说的,不是批评谁,只是又要说说而已,不吐不快。为了不至于歪曲、误解作者的意思,不怕复制具体的原话,哪怕长些,然后再谈谈我的看法。我的这些文字,在今年的七月份就已经写好,只是期末教学工作与暑假在外半是开会半是旅游,这文章也就一直让保存在电脑里,现在拿出来,还不算迟吧。 二 李文称:对余文,“我拜读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余先生在文中提出了一些新鲜的观点,认为中国书法是一种‘文化摇头丸’,书法是中国人‘掩耳盗铃’式的自慰,是中国文化阶层自愿服用并已经上瘾的、最没有文化的‘文化摇头丸’。” 余文说的原话:(开始)“书法是中国最重要的国粹之一。西方的字母文字像曲曲扭扭的蝌蚪,那是一种低级的文化;而我们的方块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书法已经升华到了审美的境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中国,题词是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拥有这种资格的人,除了大书法家之外,就是少数高级官员了。最近被公众谈论颇多的两大贪官胡长清和张二江,都是兼官员与书法家于一身的、‘能文能武’的干才。”(末了)“书法是中国人‘掩耳盗铃’式的自慰,是中国文化阶层自愿服用并已经上瘾的、最没有文化的‘文化摇头丸’。” 余文的标题表面上却存在歧义——可以有至少两种解释: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里边的“作为‘文化摇头丸’”可以被理解成“书法”的限定词,也可以理解为“书法”的表示性质的同位限定语,即李文所批评的,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摇头丸”。 李先生对于标题的解读没有错。但我希望,两人所论说的概念应该不一样。 从上下文(context)看,余杰所讨论的还是文章标题所赫然写明的“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是中国文化阶层的“文化摇头丸”,并没有真的将全部的中国书法斥为“文化摇头丸”——(文化)毒品。这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最没有用的、最无力的(似乎列宁说过的话)。而李文却说余文称“中国书法是一种‘文化摇头丸’”。其实,细究起来,两者有很大差别。我再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有过有人说,作为男人性工具的女人,你怎么能理解为“女人就是男人的性工具”呢?虽然,我们说“作为男人性工具的妓女”几乎等同于“妓女就是男人性工具”,而实际并不完全一致,逻辑上是有差异的。须知,有些高级妓女,还真不曾成为男人的性工具呢。 从上下文(context)看,余杰所讨论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涉及两个体系,“中国的文化体系”和“中国的权力体系”。 理论上,余文讨论了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书法在人类文化意义上的负面的因素,所论不详,出现个别的概念如“真理”,没有细论,李文借此说话的也有:“我们知道,社会分工是不同的。不知道这位学者提出的‘真理’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书法艺术本身创作的规律,我想书法家是感兴趣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一定是这种艺术门类的专家。但书法门类之外的知识和真理,未必就是艺术家的任务。书法家的任务是艺术创作,用优美的艺术感染人。书法家不一定是思想家,甚至也不一定是学问家,尽管我们提倡书法家要做有学问的人。要求书法家都对其他的真理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甚至精通,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就像余先生,您是研究本专业知识的,别人要求您对养猪的真理感兴趣,要求您研究修建拦河大坝的技术,要求您研究冥王星的奥秘,对您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同样,您又何必苛刻地要求书法家精通和追求其他专业的真理呢?对其他艺术而言,同样如此,您也不必要求舞蹈家去追求农田灌溉技术的真知,更不必要让小提琴演奏家去探索阑尾炎的发病机理。” 李先生可以说是有兴趣甚至有成绩于书道的,所以说了上述感情色彩很重的话,我感到这些话学理不足,尖刻有余。 而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上,胡、张二人都只能说明“在中国的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而涉及中国政治历史的诸多方面,也未能实际上也不可能在此时说清道明白,余先生毕竟年轻,做学问写文章意气风发的时候多,还不能沉稳老到圆滑,所以难免速而有漏。对年轻的余先生说到的历史事实也应该取客观的阅读姿态,尽管言词不免激烈或者过于激烈。他说:“在中国,题词是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拥有这种资格的人,除了大书法家之外,就是少数高级官员了。”没有不对的吧。 李先生则以守为攻,情状自然不一样了,文章也写得长些。 三 关于书法是“腐败的手段”问题,余文有两处,是有所特指的,并不是泛指。余文是就胡长清个案而言的,“另一方面他的书法也成为权力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成为一种极其隐蔽的腐败手段”。 余文接着又有:“胡长清和张二江的‘书法痴’并非个案。早在帝国时代,像胡长清、张二江们所从事的‘书法权力化’的工作就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书法不仅是一种腐败的手段,而且还是文化衰败的表象之一。中国人对书法的迷恋,说到底也就是对权力的迷恋,这种心态显示了中国独特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拜物教’的传统。”余文刚开头就煞尾了,惜乎申论不详。不过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入研讨之必需。书法在当权者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手段”,似乎也应该有统计依据,这就留待有心人去仔细调查统计了。至于“书法是文化衰败的表象之一”,可以存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大惊小怪,学问研究,不可能也就不要只此一家,不容许别的意见或者听不得不同意见,那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我也喜爱书法,不敢自美,但也不敢自妄,对于余先生,一个年轻人,说些不中听的话语,完全可以略迹原情。对此,李文似乎也很激动——同样可以理解,我看。 其实,文化有着时间的维度。同一个文化现象,在不同时代里边,所被用来扮演的现实角色很可能大不一样,在封建时代,书法的功用也许没有如今丰富多样,那时多为文化阶层的“雅致的”自娱自乐的道具,是品酒、赋诗、交友的日常工具,作为生财之道,谋食之法,恐怕还得自郑板桥开始算起。书法成为权利的附庸工具,那更是后来的事,就是皇帝题字,也不很长,可见的有宋徽宗的“岳麓书院”,康熙乾隆的字则是俯拾皆是,不过尔尔。至于泰山刻石,那还是另当别论吧。 如果说,书法在某种人、某种范围、某种程度成为权谋与利谋之佳途或者捷径,那是个人自家的事,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一律。我们也不必以清高姿态度之。像胡长清那样,以写字题招牌而大行其腐败之道,有社会的原因,就好像“时势造英雄”,市民世俗的文化心理状态决定了文化现象的时代表现方式、格调、品位。 这同时还说明,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过势利之交,双方都不要太“天真”,过分的天真与“自慰”,很危险。有人明码标价,一字千金,甚至于一字万金,虽然不是权贵,却胜似权贵。虽说名人并不拥有实际的权利,不是官僚,但名人却拥有民间的“文化势能”,拥有民间的文化号召力,所谓“名人效应”者也。名、权、利是三兄弟,是人都不能完全规避。 至于说,“中国人对书法的迷恋,说到底也就是对权力的迷恋,这种心态显示了中国独特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拜物教"的传统。”我感到过于深刻,我只说点浅层性的现象。城市里边,当权者的题写招牌,已经司空见惯。若说这是普通老百姓有“对书法的迷恋”和“对权力的迷恋”,那就都没有读懂社会这本大书了。就事论事,与其说这是“对于权力的迷恋”,毋宁说是对于权力的“恐惧”。作为商人,高官的题字,名人的题字,都不完全是为了美观,而更多的是追求广告效应。谁说题写几个招牌字,就是书法了,书法界有一个不成熟的共识:题写招牌原本是不入流的“书法家”做的事,所以谁也不把招牌字当作书法正品的,招牌字不过是书法的末流与小品罢了,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过去上海有专门伟人题写招牌的唐驼,就因为如此。可如今,商家已经完全放弃招牌字的艺术地位,出大价钱,请高官大吏或者名震四方的名人来题写招牌,高额的经济付出,商家获取的是权力或者名声的“荫蔽”,是一种保护伞和广告牌。说是“崇迷书法”,恐怕是抬举了人家或者自我安慰罢。 不过,爱美与企图招摇本来是联体的,不好分开,谁人会自甘承认自己是“企图招摇”而不是出于“爱美之心”呢?我例举一个人人不大高兴听的例子。妓女,恐怕历来都是时代风尚的最前位的引领者,她们追逐最时髦的生活款式,衣食住行乐,你说在她们心里,究竟“爱美”与“推销自我”哪一样是第一位的呢?不好说吧? 所以,物我两利,岂不快哉!双方寻求的是最佳的利益途径和格式(approach)。胡、张二个案,正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世俗的心理状态,书生不刊之论,不足为信。 再说一句,一些高官大吏潜心书法的研习,不能说是为着寻求腐败的途径,只是顺应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追求雅致的文化品位的心理,贪官与书法没有学理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有很多个案表明贪官利用书法为腐败的手段之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类似于事实的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法律以上的婚姻关系。李文说,“翻翻正史,再翻翻野史,尽管历代官员都有不少贪污腐化的,但靠书法发财的纪录鲜有发现。贪污受贿的手段和理由多着呢,用得着靠写字挣钱吗?说书法是一种腐败的手段,一点儿也不具有普遍性。”这是对的。 至于“书法权力化”,余文所言也几乎不差,李文申辩的也没有不是。至于写字卖钱,无可厚非,好像李先生本人的书法作品价格也是不含糊的。我要说的是,余文讲的“书法权力化”,意思其实很浅白,而李文却有点强作解人,说: 余先生逻辑是:因为自古至今都有官员特别迷恋书法,所以书法已经“权力化”。 余先生所说的“权力化”,不外乎这么几个意思:一是书法可以以权谋私。……第二个意思可能还有,必须写好字才能当官。 这就有点不大好说了,前一条“书法可以以权谋私”,未尚不成立,但没有必要细说,“一说便俗”。不过,我这里补充启老的几句诗,也许有助于双方对于这个问题的全面了解,启老的诗云:“集书辛苦倍书丹,内学何如外学宽;多智怀仁寻护法,半求王字半求官。”出家人尚且如此,何况尘世中人。 李文说:恰恰相反,很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专心于艺术,对名利和官位、权力嗤之以鼻。从古至今都不乏这样的人。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之一。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性情率真洒脱,后人读他的《兰亭序》,无不为他的超脱物外的宇宙精神而感叹。我们从字里行间没有发现他一丝一毫对权力的迷恋和向往。智永、怀素、弘一法师等书法大师都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出家人,难道和尚也迷恋权力吗? 我觉得,文化学科研究的论理,绝对不应该采取数学里边的反例法——例举一两个反例来反驳一个观点,社会科学的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统计意义上的结论,不像数学的1+1=2那样绝对,其实数学里边也有相对的东西。所以,在社会科学里边,不能靠一两个反例来驳斥一种见解、观点。社会科学的理性原则,需要大家保持冷静的态度、有效合理的应用。 至于李文的第二条“必须写好字才能当官”,我看不出余文在有意识地说这个意思,事实上当官与写一手好字,是两码事,这是小儿科的常识问题,用不着分辨,说要进入科举仕途,必须写得一手好字或者必须字写得过得去才行,这是对的。现在有几个当官的字写得很好的,过去那些字写得好、而且好的青史留名的,不是因为当官,而是因为首先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是文人当官,而不是官僚成为文人,这种顺序要搞清楚。把字写好点,甚至写得漂亮点,不管是谁,都是好事情,但官的写得一手好字,也是关系到公众形象的大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大家心里清楚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拿到纸面上去争个你长我短,任何人的所见所闻都有限,感受也不尽一样,何况还要夹带自己一己私见,问题不免难上加难,诚如一位长者所言,“学术也在永远地发展,学术的历史不能在你这里划上一个句号。况且论文中的很多材料都是靠不住的,靠一两个例子来确论一个问题不如儿戏。” 四 关于“书法也就成了文化”的相关问题,我也说说自己的私见。其实,“书法也就成了文化”的问题应该说是“书法也就成了艺术”的问题,或者还精确一点,就是“书法也就成高雅的艺术”的问题。 余文引一位学者的议论为论据。余先生是“拿来主义”。 余文借人之口笔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无文化时代人们无事找事干的一门活计,本质上属于一种手工技术,与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毫无二致,它就是一种手工艺术品。但为什么人们没有把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抬举为一门国家的艺术和国粹的文化呢?为什么偏偏是书法,而不是剪纸、木匠活和蜡染,成了文化的一种代表与象征呢?……于是乎在专制社会中,书法之风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长盛不衰,愈演愈烈。同时,科举制度也对书法提出了相当的要求,不仅八股文要写得好,字也要写得好。古人在笔记中曾经记载,有好几位才子虽然文章写得好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失去了状元的宝座。书法与仕途直接挂上了钩。人们越写也越倾情,越写越陶醉,越写越感觉良好,越写越炉火纯青。久而久之,书法就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形式取代了内容、书法取代了思想。于是乎国人一流的智力、一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绝大部分都‘主动’投入到书法的‘事业’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风雅’、最‘高贵’的书法也就成了文化的空洞和文化的假象,同时它也被招安在权力网络中,参与了规模庞大的‘愚民工程’。” 李文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愤不平。 对此段论述,李文花费了很长的文字来批驳。李先生批评说: “余先生身为高校教师,没想到竟然对这段逻辑混乱的文字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并拿来做根据。这段话虽然不长,但错误百出,概念凌乱。混淆了文化、文字、书法、文章、思想等含义不同的概念和它们的功用。” 可见李先生的愤激之情,李先生本来就是可以明码标价公开鬻字的书法家,难免护道的心情。不过,书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的艺术形式,大家可以坐而论道,不可以感情用事,剑拔弩张,怒目相向,从学术的角度看,“Fair Play”要提倡。 说说我自己的看法罢。书法是雅致的、高贵的、中国式的艺术形式。说它雅致、高贵,不会引起太大的误解的。中国的诗歌难以言说和解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书法艺术更是“道可道,非常道”,更加没法说清楚的。“英国皇家学院的首任院长雷诺兹作过一系列著名的讲演,他觉得艺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用,可以把社会改造得更加美好,更加道德化。他在一次讲演中引用了他的同代批评家哈里斯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吃惊。哈里斯说,想让一个人进入高雅的艺术,或者说你自己想进入高雅的艺术,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假装喜欢这种艺术。”古人出于实际的需要,要写字,没有别的如今天的录音、电脑输入之类代替方式,所以不会写字的人,那时是难以进入主流社会的,登科取士,更不必论。所以,实际上几乎可以说,起码是在后来,书法本来只是封建士夫的应具备的基本技能,以时下的说法,那就是基本的素质,读书人不会写字,那是可笑的,就好比木匠不会磨斧头,裁缝不会理针线,厨师不会切菜,有时还很可恨,很可怜。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学子的启蒙课程,描红习字与读三字经,同样是人生的基本之基本课程。至于摹习前人的书法比如唐人的楷书、魏碑的刻字,对于人的个性养成会有什么样的好的、坏的影响,显性的、隐性的,都不是三言两语所可尽道。是不是也有像哈利斯所说的、或者近似的情形在其中,大家可以深入研究,不必急于下结论。有位年轻人的话或许可供借鉴,他说:“我想我们应该避免任何武断的结论,比如说,《蒙娜丽莎》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倡导世俗生活的独立价值,把人从宗教的氛围中解放出来,等等。” 两位先生都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书法不独中国以及流传过去的日本有,不独方块的汉字有,别的文字也有书法。只是中国的书法艺术的在中国文化里边的地位特别突出,非其它文字化文明体系可比拟。那位学者的议论,一方面使其所见,一方面是他的分析见解。从学术的角度而言,研究者没有自己的体察和理解,没有自己的发明(discovery),那就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那不如去照本宣科,还不如误人子弟强。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私见,余文比李文更有味道,更值得玩味再三。 李文中说:汉字属于方块字,其笔画的排列组合具有回旋余地大、千变万化的特点,而书写工具——毛笔的笔头较软,书写的线条又具有粗细、浓淡、涩疾等丰富变化的特点(正所谓“笔软则奇怪生焉”),再加上书写载体——纸张的改进,也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更大的驰骋空间。这些客观因素是书法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汉字书写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不是别的原因,是由汉字的特点和汉字书写工具及书写载体的特点决定的,汉字和汉字书写工具的特点自然而然把汉字的书写引向一种艺术的范畴。之所以剪纸没有成为国粹,而书法成了国粹,就是因为书法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艺术魅力更加强烈,根本不是什么“天大的误会和骗局”。 至于“剪纸没有成为国粹,而书法成了国粹,就是因为书法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艺术魅力更加强烈”的问题,我想谈点感想。 书法,与生俱来,与文化和文明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主要的承载工具——文字形影不离,而剪纸和蜡染不会成为文人士子争相学习的艺术,就是因为它们之间的文化所隶属的层次大不一样,雅与俗的分别,在于文字所能容纳的思想感情之多寡,秦始皇要统一文字,意义深远,尽人皆知。我们的书法作品,写的是什么,与剪纸和蜡染的画图内容比较,一看就明白。所以,书法是文化人的事业,是高雅的文化艺术形式,是不去附庸高雅的东西,所以人们争相摹习书法,而不是学习剪纸和蜡染,因为书法的最最基本的要求是文字。 再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综合的文化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为士子儒生)要能入世又能出世,书法的艺术的、思想的、情感的表现方式正好切合人心的需要。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不是追求透明的、意义唯一的,而是力求意会的语言格式,不是显函数形式的,而是隐函数形式的,甚至是复合的,所以才有中国乃诗的国度一说,所谓“诗无达诂”,书无定评,就是因为这个。儒家强调入世的态度,所以要说,不立文字,不罢休,可道家的处世模式,又要求人们规避、藏而不露。书法恰好满足传统士大夫的这种交流交往模式的需要,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手扎,碑志,连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摩崖石刻,诗歌唱和的多了,哪有什么关乎民族国家社会人生的宏论,即兴小品文。所以,最好的见证是,书法乃修身养性之佳途。 书法作品里边表现的人文个性与精神,所包含承载的人间情怀,审美价值取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很难切实的解构。也许许多的作品诚如一位古代诗人所写的:“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所以,观者只能见其表难以察其里,我们往往易于强作解人,难免自作多情的臆说。我们不妨看看严嵩的字迹,乾隆的书法,如果我们被实现抹去作者名姓,那就会闹出大笑话。君若不信,大可一试眼力。 李文又说:至于极端的专制主义,如文字狱的条件下,也确实会使一些学者潜心于金石书画,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这些艺术和学问的发展,但是其中的作用是很小的。而且,极端的专制主义由于禁锢人们的思想,创新的艺术也同时会受到禁锢。从历史上看,这种观点也不符合实际。唐朝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时期,尤其是唐代的前期和中期,专制主义的气氛并不浓厚,像唐太宗这样的人还能听进去反对的意见,但是唐代的书法艺术却是书法史上的高峰之一。“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典型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那么,按照这段文字又说,“许多‘伟大’的书法家对真理没有兴趣,而终生沉迷在书法这一变态的‘美’中。尽管他们在书写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界,但他们本人在文化的意义上依然是一个‘文盲’。” 李先生这段话似乎说服力不强,因为“靠一两个例子来确论一个问题不如儿戏”。而且,李先生的话好像没有说完,以唐朝为例,又接着以“文革”为例,想说些什么,怎么欲言又止了呢?“不可说”。 我这里隐隐约约感到,李和余两位各自心中的“文化”,论质地,是不一样的,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说实在的,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一词,是最难捉摸的一个概念之一,所以许多人都是“欲说还休”。 五 再来说说“摇头丸”的比喻罢。 李文写道: 作者把书法家阿臜了一阵子,于是得出结论:书法是中国人“掩耳盗铃”式的自慰,是中国文化阶层自愿服用并已经上瘾的、最没有文化的“文化摇头丸”。摇头丸者,一种毒品的名称,作者如此来表达对书法的憎恶,可见其对书法的痛恨程度。 把书法比喻成摇头丸,是余杰先生的很猛的一个发明,我觉得。说摇头丸是一种毒品,太普通了,普通得几乎没有意义。摇头丸这玩意儿,据电视上的报道可知,是一种兴奋剂,似乎还是简单些的,厉害的还有冰毒等,现在中国人难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觉得现代化不够水平,另一方面,又觉得传统的东西几乎算是丧失殆尽,感慨良多。就书法而言,矛盾心绪也有所体现,不过弘扬传统文化,似乎还真只有从京剧和书法两者着手。京剧太过需要技巧,难于普及,书法则不然,简单些,一支笔,一张纸,即可开张,甚至于纸笔全无也没有多大关系,画地也可以习书,所以让人学习书法,极为简便。在普遍感到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正在衰落的今天,如果推广书法能起到振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那就比作文化摇头丸,也未始不可。我担心的倒是,书法在今天这样的社会,要担文化传承的角色,恐怕是我们有心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就我所见,大人小孩,学习书法,多少带有功利的目的,开设书法班也流于一味的扩充经济效益。个中的具体情状,当事者暖冷自知。 李文又说:摇头丸者,一种毒品的名称,作者如此来表达对书法的憎恶,可见其对书法的痛恨程度。 难道余先生真的这么痛恨书法?学术研究就真的这么密切的关乎实际生活?没有亲证,我不敢信。也许余杰先生还有深意在焉。总之,还要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才是。 六 李文第二段说:由于余先生是个比较有名气的作家,又在名牌学府北大教学,这种学术和真理之外的光环和位置很容易给人以误导,为了不使谬误影响初学者和青少年…… 我要说的是,余先生的文章恐怕(!)是“少儿不宜”的,或者说,余先生的文章应该没有专为“初学者和青少年”而写的意思。所以,李先生这一担心就显得多余。如果一篇文章就能有这么大的效力,那中国文化人的威力就实在吓人得紧呐。我看,学术研究,不能动不动就搬起“初学者和青少年”来,这样做似乎太幼稚了。以“初学者和青少年”作为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研究的准则和标准,在青少年方面的问题上是无可厚非的,文化研究也以此为鹄的,那就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对于“比较有名气的作家而又在名牌学府北大教学”的余先生更是不公平的(虽然余先生还不是北大教授)。 就我所知(很有限),余先生好像还没有专门为中小学生写的文章,是否有兴趣和时间呢?吾不知。 下面是一位教授的演讲,也许对于读者理解把握余、李之间的论争有些帮助,他说——“人们为什么附庸风雅?我想它反映了一种愿望,反映了人们想竭力摆脱俗气这么一种处境,或者说想摆脱自己的趣味低劣这么一种处境,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种愿望导致了人们去附庸风雅——我国的沈从文先生也由此说。在19世纪的末期,维也纳的音乐界分成两派,一派是勃拉姆斯派,一派是瓦格纳派。瓦格纳派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斗士,也是一个作曲家叫沃尔夫,他听到有人在赞美勃拉姆斯,便气愤得一屁股坐在钢琴上说,你们看,我就是这么弹勃拉姆斯的。可是有一段报道说,沃尔夫去听了勃拉姆斯一首交响曲的首演,出来后喃喃自语道,天哪,真让人喜欢。这就是说一种情境把你带进去以后,你自己就觉得你是里面的一员斗士,一员战将,自己也不问这件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叫好的时候,你就跟着欢呼起来了。任何一个体育迷恐怕都有这种体验,艺术体验也是这么一回事。比方说在文学史上,伏尔泰曾经攻击过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的东西是滥醉的野蛮人的东西。这是伏尔泰在他的一个剧本的前言当中写的。在这种艺术体验当中,人们往往看不清对方的一些优点,或者对方有些优点干脆不看就把它扔到一边了。我举伏尔泰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们想摆脱俗气,因为莎士比亚是低俗的,是野蛮人的东西,而法国古典主义的东西才是高贵的。难怪著名演员加里克为了使莎士比亚高雅起来,甚至冒着观众向他扔凳子的危险,不但删掉了《哈姆雷特》的掘墓人一场,而且还为《李尔王》增添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是附庸风雅的第二个方面。 附庸风雅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导致了另外一种嘲笑的体验,一直嘲笑到什么程度呢?一直嘲笑到大家都不喜欢它为止。美术史上的一个画家,他的名字叫瓦茨,他在英国19世纪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可是后来已经大为黯然了。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切斯特顿的人想为他树碑立传。切斯特顿已经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写瓦茨的传记时就说:有时候,沙龙里的一声低语,也让一个伟大的东西突然变得陈腐。这种低语有时候确实就是以嘲笑这么一种形式出现的。拉斐尔作为一个绘画王子被人拉下他的宝座,就是因为一代一代人嘲笑的结果。他们嘲笑他的圣母太漂亮了,我们知道,太漂亮有时和俗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之所以引这段文字,因为书法也是艺术,而且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反思这段艺术的形成过程的时候,这种姿态或者观照的方式与角度或许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有点帮助。 七 最后一点补白。 李先生很认真的人,对于余文“我拜读了好几遍”,我觉得余先生自己也会感动的,这是对于作者和文章的厚爱。 感谢网络文明,我在李先生文章发表的当时就阅读到了,而且马上想到许多东西,现在写下的,是当时的阅读感受,旁注和眉批的部分,有些话是李先生和余先生的同义反复,就不说了,余先生很富灵感,李先生很富热情,愚不及一一。 我想在李和余两位,都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有一种观点,即“书法,小道乃尔”,我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化里会有如此尴尬的情状。 沈从文先生的话可能更见宽厚的长者风范,他说:“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是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也许能帮助我们消解彼此间的隔膜。 再说,书法也要与时俱进,传统的固然好,但没有时代的新内涵,也不好。举一个例子以资佐证。当年,翁方纲批评刘墉的书法,说:“你的字哪一笔是古人的?”刘墉反辱相讥:“你的字哪一笔是自己的?” 所以,历史公案,清官难断。 【回到首页】 【我要发言】 【关闭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