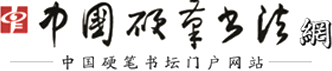书法的疆界 马啸
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书坛各种冠以“现代”之名的展览层出不穷,但从来没有真正对传统书法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具有近20年探索历史中国“现代书法”(姑且这么称呼它)运动,实质是一个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规模与影响力极有限的实验形态(之所以说它是“实验形态”,是因为它至今仍十分地不成熟),它对于那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了无尽深邃精神与形式内涵同时又沉积了众多习性与惰性的书法传统,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震撼。
这是事物的一方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些不成熟的艺术探索,愈来愈深刻地接触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书法有无疆界?”或曰:“书法的疆界是否有必要存在?”便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实质问题。
提到“疆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初欧洲“达达主义”的创始人杜尚。这位现代派美术的重要代表人物,1917年因将一个小便器实物直接签上自己的大名(命名为《泉》)送去展出而名声大噪。自杜尚的《泉》诞生至今已有八九十年时间,世界艺术的格局已彻底发生了变化,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那堵高墙已彻底坍塌。这种坍塌自然也激起中国书法界许多“仁人志士”的梦想与欲望。
在许多前卫人士的观念中,艺术的现代性首先在于规则的打破。他们认为书法固有疆界的存在,是导致中国书法无法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打破书法的疆界,将其外延拓展到书法以外的形态之中。于是,他们借助装置、借助现成品或是别的什么材质或手段。
作为一门生存并发展于现代社会的“活的艺术”(而不是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艺术),外延的扩展是很正常的,况且,书法的新形态本身就是还处于实验之中,游戏规则打破一点,或者另立一套,都是可以的。但书法的根本发展,书法能否迈向现代,绝对不仅仅靠“现代”二字就能解决问题的。如果真正站在“书法”(而不是“大艺术”)的立场考虑问题,真正为着书法的前途着想,笔者以为,无论一个探索者的设想如何大胆,步子迈得多大,还是应该在圈内,否则,纯粹变成一个装置或是其它一个什么东西,就等于取消了书法。真正的艺术的现代性,绝对不在于靠推倒先前的法则跳出固有圈子(或疆界)就可以得到;更不是外延越大,当代性就越强。艺术的疆界就像一幅画的画框(这里不是指实际镜框,而是指一幅作品的边界),真正要使一幅作品与众不同,首要的不是将那个画框取消,而是要使其中的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当然,你也可以别出心裁,将画框设计、制作得别致一些,或者虚化这个框架,但绝对不是要取消它,否则我们就不知如何将它呈现出来。我相信,在疆界之中不能使自己的作品变得“现代”的作者,即使跨出这个疆界也无法使自己做得更“现代”——当今中国书法之所以无法“现代”,仅仅是我们的想象力或操作能力不够,而不是我们的材料不够或做法不够极端,这就像盖房子,古代人用木头、砖块盖的是古代的房子,我们现在还用这个,盖的却是现代样式的房子。这里,有一个原则性的前提,就是房子还得具有房子的功能,不论它的样式如何变化,外形如何稀奇古怪。
正像陈振濂先生全力主张和倡导“主题先行”一样,如今书坛的许多前卫人士非常关注作品中的精神性因素。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错,因为作为书法,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始终没有将作品的主题思想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我们如此定义,并不是说传统书法中,没有精神性因素,只是说这种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非自觉的,或者说,多数作品是在成形后才具有的,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其精神涵义其实仅仅是文字内容。或许是出于对此种情形的反拨,书坛那些前卫的“有识之士”们格外重视精神与观念,并希图以此支撑起梦寐以求的书法的“现代性”。他们是如此渴望书法的现代性,以至在自己的实践中“现代”成为了比“书法”更为重要、更为实质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现代书法”不可能把“书法”当作主语来看待,它只是一个定语,“现代”才是主语!
很明显,为了“现代”二字,他们可以让“书法”变成一个奴仆,一种辅助——一个实现“现代性”的工具。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轻而易举地理解,为什么在如今多数的“现代书法”家的作品中没有笔墨,即便有笔墨也不易让人找到其中的功力、内涵与形式之美感。
1997年初陈振濂先生刚开始倡导“学院派”时,笔者曾在杭州与其进行过探讨制作与书法的关系问题,它实际已涉及到“书法的疆界”这个问题。举个例子,一本字帖放在那里是书法,但当我们把很多字帖都贴在一个画框里(可以搞各种创意),然后画上各种线条、各种符号(如康定斯基或米罗的线条和符号),或涂上各种颜色,即便这种线条或颜色并不妨碍字帖中书法韵味的展示或者使字帖更丰富、美观,但那样干的结果,只能使书法被削弱或者被取消,因为那时,只要你有一点点审美眼界,都不会将其再视为书法而是书法以外的东西,如招贴海报、书籍装帧,甚至装置作品。
近年来,在书坛那些溢出书法界限的作品中,有3人的作品留给我了一些印象,其一是1995年夏于威海举行的“第二届书法主义展”上洛齐的4件现成品。它们均由左右两个面积相等的部分构面,一侧为外文印刷品,一侧为书法类报纸或字帖、图片,两部分之间以上、中、下三道墨线或纸片连接,作品中,除了简而又简的三道连线外,看不到任何笔墨操作的痕迹。
在此之前,1992年,王南溟开始推出“字球”组合作品。“艺术家本人书写的一幅幅传统书法作品被揉成字球,堆积如山或随意摆布,意在批判和否定传统书法创作,让观众在震惊于书法家无意义重复劳动的同时,思考传统文化符号在新时期的再利用价值。”(引自《中华艺术界》网站)这是一件操作过程简单但极费时的作品,据说作者请了不少人先将字写在宣纸上,然后再一个个揉成团。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位理论先行的艺术批评家此后似乎再没有推出新的作品,每逢有展事,只是将这件“代表作”重新搬出而已。
“踪迹学”是张强这些年独创的一个新词,我不知这是一门新的学说还是一部新作品的名称,但是它的轰动效应是肯定的。书法发展了数千年,书家们将字写到了甲骨、金属、木头、竹片、石头、宣纸、布片甚至墙上,却从来没人在人体(特别是亮丽的女人体)上直接泼墨(说它是泼墨,是因为观众见到的污秽的墨迹而没有一丝的书法感),并且将这个过程展示给人们看。将东方的神秘主义与西方的人体展示、性别文化融为一体,自然会叫人惊诧万分。
上述种种行为是“书法”吗?这些行为的结果是作品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本质主义”是这些年备受书坛前卫人士攻讦的一个名词。关于这个词,我不知如何确切定义它,只知它的一些基本所指:坚守书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则,如笔墨、书写性、汉字或类汉字结构,等等。如今,“本质主义”已成为书坛保守派的标志性特征。
有必要申明,我们虽反对那种漫无边际的观念宣泄、反对将书法从形象变成纯观念的东西,但并不反对观念本身。事实上人类及其艺术的每一次演进都是观念作用的结果,没有观念的改进我们可能永远徘徊于黑暗之中。就艺术史考察,观念与艺术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比如书法,观念的改变会促使新书风的产生,同时,新书风形成后便会更好地传达一种新的观念。而一旦有了新的观念,我们眼前的世界便会变得迥然不同。也正是站在这种立场上,我们说,即使常规的书法也可以生长出现代性来,比如刚才提到的甲骨文书法,由于其文字之间无意识的排列组合——不计多寡地三三两两分布,而不是遵循后来常见的顺序排列法则,这种情形极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现代感——如跳跃、断裂、错位,还有残缺。当然它不是现代思维的产物,之所以我们看这种东西很现代,首先因为是作为欣赏者的我们观念中有个指向。没有了这种指向,也就没有了艺术。
“现代”与“书法”是一个困惑我们的难题,“所谓的‘现代书法’,它不可能从‘书法’走向‘现代’,只能是‘现代’走向‘书法’”(汪永江语)。这是当下书坛思索者极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举出日本“少字数”书法的例子加以佐证。据说“少字数”书法就是从西方表现主义的立场出发走向书法的。笔者不曾研究过“少字数”书法,但依自己及周围人的经验,书法家们可能无法做到像建筑设计家那样,先画像一张图,然后按图施工。因为书法作为一种徒手作业,许多精神性的东西要在身体力行的笔墨实践中才能产生,并且还是要在这种实践中才能升华。那种先在的创作指导思想肯定是有的,但却是非常模糊的,它无法决定一位书法家作品具体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只有在“创作”与“观念”的不断碰撞之中才能得以确定。所以,我们说,所谓从“现代”走向“书法”的观点是缺乏实践根据的,因为很显然,人们不可能先将观念探索得很清楚,然后去练书法;或是先从观念出发将作品设计出来,然后再着手创作。
那种认为凡坚守书法“本质主义”立场必无法使书法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观点,无疑是小看了书法本身的表现力,或是将书法的“本质”看得过于狭窄,认为书法只能表现那种古典的情绪,搞书法只能像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或其他传统书法家那样写字。自然,像王羲之那样写字永远不可能写出一个“现代型”的书法家来。
书法是一种既定规则下的游戏,而“现代书法”则是另一种规则下的游戏,前者产生并生存于传统语境中,后者产生并发展于现代语境中,所以两者根本无法找到对应点,换句话说,“现代书法”根本不可能从原有的“书法”中生长出来,所以得从“书法”以外的东西中找出路。这是当下一种极典型的书法现代主义主张。
书法并不需要如此悲观。就像地球本没有生命,但生命就可能产生在地球上。为什么?一个惊雷打下来,产生了化学变化,生命从此开始萌芽。顺着这种思路,书法的现代性完全可能在原先的笔墨纸砚中产生,说得更简单一点,它只用黑白两色,最多再加点红就可以产生出来。当然,要使书法中产生出现代性来,必得修正我们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另换一个)。这让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广泛兴趣的学术命题,叫做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当下,中国书法就需要来一次创造性转化,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现代”起来。所谓转化,就得利用原先的许多东西,然后再注入新东西,使它激活并发生反应。而要注入新的东西就得要修正规则,起码我们应将原先的那个传统视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只有有了这种开放,外面的东西才能进来,里面的东西才会被“激活”、才会有“反应”。那种对书法的现代性放弃希望的人,首先是将书法视作为一个死规则,并不允许它进行修正,所以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在“书法”的地界以外搞所谓的“现代书法”。结果怎样呢?没有了笔墨、没有了结构,论形式赶不上设计家,论观念比不过前卫美术家,制作出的东西书法圈内的人不喜欢、圈子以外的人同样也不喜欢。
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李旭曾对那个由自己策划的“2002上海双年展”无奈地说:“当代都市艺术在表面样式和内在精神上也正在面对着逻辑上的悖论:首先,带有强烈观念性的都市新艺术作品与日常生活本身之间的疆界正在湮灭和消失,大量粗制滥造的装置、行为和录像作品正在败坏着当代艺术的名声,从而导致近十年间对‘皇帝新衣’式艺术现象的追讨之声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艺术疆界问题所带来的危机,不仅是中国的话题,更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话题。其次,大量表现都市的作品在语言和手法上完全滞后于都市本身的发展,作品内在精神深度的普遍欠缺使所谓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或者完全成了庸俗时尚的帮闲,仅仅为晚报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些奇闻怪事的谈资。”(中国艺术品网www.cnarts.net)
一个最具实力与权威性的上海双年展尚且如此,不成规模的中国“现代书法”离成功之日更是遥远。
笔者近年来曾参与、参观过为数不算太少、规模不等的“现代书法展”,但多数展览的情形让我失望。一些原本笔墨功夫很好的作者们为了使自己的东西更“现代”,使出浑身解数,唯独遗忘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这样,一个现代书法展恰似一个“比短”竞赛,搞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一张脸孔,相互消解。本来现代艺术就是要展现作者无限的想象力,但如今大家的思维好像都枯竭了,都走到了一条路上。没有个性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同样,没有难度的艺术最终也是不会长久的。西方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有一部分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更多的东西具有相当难度,非专门家不易把握(所谓的“削平深度”是另有所指)。中国书法,本来外表相对简单(实际是单纯),现在人们又把它的结构、笔墨中微妙的东西消解掉了,最后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不剩了。单就这一点来看,中国的“现代书法”的前途就不容乐观。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定近年来中国书坛在“现代性”实践中取得进步,像王冬龄、邵岩、白砥、陈大中、张羽翔、汪永江等人的实验性作品,甚至北京“流行书风展”中的一些作品都具备了既是“现代”的又是“书法”这双重要素。这些人中除了邵岩的部分作品更多地接受了抽象绘画而与书法相去甚远外(他可能对此类作品格外偏爱,但我们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西方美术家如罗伯特·劳恩内、雅克·维隆、彼埃特·蒙德里安的笔下已屡见不鲜,所以在我看来其艺术意义远没有他的那些用笔或汉字构筑的作品来得大),其余书家基本在“书法”这个“本质”范畴内行事,他们不论是探索性实验还是成熟的艺术实践,都在努力拓展自己的艺术外延,对传统书法的既定规则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只不过还没有溢出“书法”的边界,所以我们还可以在“书法”的范畴内来讨论它们。或许正是这一点,这些人的作品获得了更多的认同。
思想可以无疆界、观念可以无疆界,甚至艺术也可以无疆界,但书法不能没有疆界。就像技术不是衡量艺术的首要标准但技术的难度却在保障着艺术的生存、深入与发展一样,疆界是书法之所以成为书法的必不可少的保障。无论你的作品是在呈现形式或是纯粹指向观念,但那条“书法”的边界应该存在,否则它不可能是书法,也绝对不会是书法。
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我们无法断言书法的最后疆界必然在哪里,但如果书法尚继续存在的话,笔墨、书写性、汉字或类汉字结构是它必然要坚守的底线。
2004年8月改定于兰州
来源: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