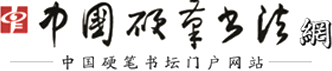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大研堂谈艺录》是我近几年来从事创作和教学的纪录,有笔谈和学友记录整理,比较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了我的理念和道路。有关书法的已部分发表,这里选录的是关于篆刻的部分谈艺录。
一
流派篆刻风起,以文人才情个性独煽印坛,轰轰烈烈五百年。风骚者个性也,传世者亦个性也,无个性之印风则无印史霄羽之迹。风啸啸以独擅,声涛涛以众攘,派者当有独擅与众擅之成。流者,派者之趋也。追求个性语言,掌握话语权,流派之使。多年吾于印之道,留意印坛之变化,思已之行迹,起伏上下而有所悟,仍不敢懈怠一刻,恐与人同,恐与人似,恐与人非,恐与人不为,离群而不离时,求新而不求奇,求意而不求趣,斯是吾之啸声也。
印者,心印也;印者,印之匠者,金石锲也。为印者,以铄金振玉之德为德,开化胸襟,不囿成见小己,而振新我。为印者,当以心性之外放,敛于体素,视做作为手段,不以做作为做作,心性随天也。故印者,行走坐卧为行走坐卧,而非行走坐卧;求与他人之不同,异类也。复为行走坐卧而行走坐卧,斯可出匠也。
印者,印也;印者,刻印者也。孰为清浊,不明非明非清也。
印者,当知印之流变,承印之传递,能抚古鉴今,推古出新,方得有源之水,涓涓无尽。
诗书画印四绝,以印为最难。印之为印,必有书意,变构思,取意境,方得其真,得登堂奥。欲为印者,当识之。
印从书出,须有书意,运以流动,得以线质;印以画入,变在构思,图以形式,画以构成;印从诗新,化其境界,廓其空想,联其感悟。斯是印之旨也,印当为四绝之首,非吾之大言矣。
刻印与文同,当以神采为上。神者意也,采者饰也。饰可求,神得养耶,无颐养之功,何以言艺。刻印出于本性得于后天,印方有神采。
二
从印章传世和出土实物来看,古代印章在实际用途中,朱文印章使用频率大大高于白文印章。白文印章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是铃盖在封泥上,因此传递给阅读者的视觉感受依然是“朱文”。从印章在历史过程中的凭信作用来看,印章从产生之初,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公章,朱文的使用仍是主流。对秦汉以前的印章的具体使用方法,以及在封泥没有被广泛运用之前的印章铃盖方式,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求。特别是古人对印章在不同的使用环境中的视觉感受的差异,并由此而来的对古代印章中朱文、白文体系的形成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某种意见上讲,白文在古人的使用过程中一直是以“朱文”的面目出现的,它传递给阅读者的初衷是“朱文”的视觉感受。之所以呈现出我们今天能认识的白文面貌,是宋元以降,金石学家和印人对古人印章使用方式的茫然所造成的。由于按捺于封泥之上到铃朱于宣纸之上,物质载体的不同,造成了后人对前人的“误读”。正是因为这种“误读”才造成今天篆刻艺术的多姿多彩。
战国有很多朱文小钅尔,烙和戳是其主要的使用方式,这可以从出土的漆器、陶器和金版上看到。在这种使用环境中,朱文更清晰,更好使用。最早的印章是工匠在制作器物的过程中便于戳印花纹、图案而产生的,并逐步过渡到文字,亚美尼亚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文化现象。包括一些汉砖中都出现了印章使用的痕迹,这是印人应关注和研究的东西。
朱白文在古印章和明清流派印两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体系。一种体系是粗白细朱的线条,这在古印章和流派印章的前期作品中屡见不鲜;另一种体系是吴昌硕、齐白石先生所开创的基本等粗朱白文线条。在第一种体系内,不管是白文的粗线条和朱文的细线条,不能忽视的就是古人对红色的重视。粗白文的留朱与朱文的线质是一脉相承的,其区别是视图的方式不一致。如果排斥文字识读的努力,只关注视觉感受的话,整个印面的红色线条所构成的关系就形成了这一体系的基本脉络。另一体系,吴、齐二人不满足于线质只停留在对古代印章的解读与延续上,对印章的朱白文线条的外部形态的统一进行了全新的尝试。明清流派以至西泠八家,都强调习古,始终没有摆脱对粗白细朱体系的依赖。吴、齐二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把线条改造成为一种新的体系。这是篆刻完全成为文人化的艺术的一次革命。篆刻理论界对这种艺术自觉还没有给予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他们改变了五百年来篆刻的创作表现,重新界定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
组印作品削弱了篆刻艺术的独立品格,成为语言艺术的附庸和再现,它强迫欣赏者做出文字识读的努力,甚至仅仅停留于文字识读,严重削弱了篆刻本体的艺术魅力,因此,组印作品也难以称之为有主题的艺术创作。第二层面,即艺术作品中诉说企图和表达冲动与艺术家本人生存状态的关系。艺术作品必须反映出艺术家个人在当下的艺术状态和心理轨迹。即如我创作的“大研堂”、“腕底有鬼”“抓鸟去”、 “与狼共舞”等印,在边款中记录了大研堂新址入迁记等多篇反映我当时心理状态的短文,欣赏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知晓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起因、构思乃至喜怒哀乐,通通都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艺术品一定不能脱离艺术家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技术,艺术的技术化,是艺术家从艺理念的分别,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左右的结果。炫耀技术和把技术简单化,带来的就是浅层次的审美感受。对裸露、崩蚀线条的过度推崇,而忽视对线质的控制也是技术化趋向的另一表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有些作品一、两件还可以,到后面就不行了的主要原因。作品让你感受不到“人”的力量。
当前对技法的丰富,很大层面上是在对印章的“做”上,传统的篆刻技法是以“刻”为主,到吴昌硕开始把“做”作为一种必要的技术手段运用于篆刻创作。吴昌硕的伟大就在于,他第一次在篆刻创作中大强旗鼓地提出了创作后期“做”的必要性,到了今天,把“做”堂而皇之地纳入到了篆刻创作的过程中,这是一个贡献。
制作的问题也有雅俗之分,这涉及到篆刻家的从艺经历和艺术修养。雅从古来,王镛从古代砖文找到自己的线条语言。韩天衡的“做”传承了吴派的一些手法,用“伤害性”的手段对印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做残。而石开的制作是很细腻的,招数很多,表达了古印章线条的质感。可以说“做”己经成为当代篆刻不可缺少的一种技术手段。
研究古人是为了传递古法,用古人的方法进行创作,这在陈巨来先生的创作中得到过较充分体现。其他的篆刻家基本不这么用,这与文人对篆刻艺术的参与以及篆刻的艺术性与工艺性定位有关。文人的艺术状态,始终是排斥工匠和技术化的,追求的是一种率性而为、性情所至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中国文人艺术一以贯之的审美心理。
“印从书出”从清代被提出,到现在都是印人的印学基点,赋予的内涵随历史的演进而扩大。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以印人自己形成的具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新的具有个性的印风。”(引自黄惇《中国古代印章史》)二是,从书法文字演化过程,寻找适于入印的文字,并以具有个性的印风,使之配合。三是,用刀如用笔,用刀如写,印有笔意书意,书印合一。
三
甲骨文入印既要见刀又不得外露,用铸铜之法敛之,方能于峻峭凌利之外,有浑厚之气。
古钅尔在高古之风尚中,以诡异秘密为胜,常常神出鬼没,收发无常,不可端倪。吾恐不能悟妙,故在诡里寻正,异中求变,合高古之理想,而取雅正之平常。
汉砖镜铭诏版文字,纵行求通之势,盘绕转合之体,省减为变之形,与缪篆同,各为一道。若入印,当是奇异、峭拔、宏博,别裁新机也。
汉印以铸为凝,含蓄而真力外溢,以凿为放,灵动而刀意冲和。取汉法者,多择其好,见刀者得古峭,见力者得古朴,复有古拙、古雅、古趣等传递汉印之精神,而立门户。
白石心思。白石上接三国魏晋,下续二金蝶堂,以单刀法在五百年流派中,独擎大帜,开齐派之风流,而引当代之时风。以木匠之短变木匠之长,单刀直冲胆气壮,勇猛直行任我爽,淋漓痛快,胸襟自现。
何止三百。白石老人自诩“三百印石富翁”,小子言“何止三百”。噫,言罢诧矣。三百为数也,三百不数也,三百者言数而无据,取意于心不在意。
齐派篆刻单刀直入,线条太裸露。齐白石很历害,用制作的方法解决了线条裸露的问题。他用的印泥,是自制的,油多砂重艾丝短,可以很好的模糊一些线条过于迸裂的痕迹,增加其印章的浑厚之气。印泥的作用异常关键,这一点后来的齐派篆刻家及追随者很多没有注意,所以作品的线条地就越来越裸露,越来越缺乏意蕴。
临古钅尔印欲求形似,往往细啄轻剥,施以小切刀法,唯恐劲过而伤残,其中度颇难把握。先放松心情后移至手,心手相协,尔后刀不宜碎, 碎则劲道被懈,著此即成。
临印有二,其一遵其形而入其意,其二尚其意而随其形,此二境界只是先后而己。临印当在第一种,欲求第二境界,从刀之爽来寻之,自是心得。
刻汉私印,易雅致,易清明,易圆润,劲健尤为难得,张力稍大则收敛不够,难在敛之意。
黄氵睿《尊古斋古玺印集林》收录“路右攻师”印,结字安排甚奇,与六国青铜鼎彝铭文极似,乃为入印之先河也。
郭裕之《续齐鲁古印攈》藏“易□邑□□蒀之钅尔”钅尔之代表,仅存。此钅尔布印犹有书意,流动生姿,秩序有度。
创造性地临印,将原印构成基本元素进行强化组合,获得新形式,新结论,充分体现现代之表征,开拓印治新追求。
汉未至魏晋南北朝之印风,为衰势,当不可学不可为。
松散是印之一病,亦布印之一法,非大智者不敢为。钅尔印中常用松散之法破紧密之垒,出奇制胜,黑白世界,得其髓也。
刻圆朱文印,须通篆法。文三桥、林鹤田、赵扌为 叔于篆成一家之规而言印,即印从书出是也。斯冰之后,篆法在清完备,于近现代得 以巩固发扬。欲求篆法当从斯冰问起,方有高古之气息,近可学方介堪、韩登安,此法可得矣。
明清以降,用刀莫过冲切二法,然冲切之辨格,各出奇招。雪渔冲之坚挺,钝丁切以尚古剜,完白冲切结合以效书,隽唐、攘之刻以弧冲厚,秋堂、小松、曼生切之以剥,扌为 叔冲之以铸,牧甫刻用凿金,白石冲之以木,以上明清诸家用刀皆用推凿之法。
牧甫用刀为薄刃,其法是清底后,薄刃于线侧重走一次,线壁如墙,劲挺有力,铃盖印泥也不宜漫没。
四
当代人对现代篆刻的理解和探索,也是“流行印风”中很多人在追求的东西,这些作品往往给人第一感受还是不错的,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但缺乏一种印面之外堂堂正正的正大气象。当代篆刻对刀法和字法的探索,己经远远跨越了前人篆刻艺术的藩篱。正如陈国斌先生在教学中提出,篆刻就是用刻刀在印石上进行画线,将情感的宣泄直接诉诸印面上。这种观点的益处是大大开拓了篆刻家创作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打破传统篆刻技法传承后,对文字的印化和篆刻技法的深刻轻视。
作为一种创作理念,我也非常认可陈国斌先生的主张。他把篆刻放到了一个纯艺术的定位上,重在启发每一个人心底的艺术冲动,从篆刻艺术的起源来说这是正确的,正如先人在岩画中传递出对生命最本原的艺术表达。他用原始刻画的简单方法把艺术天性启迪出来,摆脱了对艺术的神秘感。他尝试建立一套全新的篆刻创作、教育、传承体系,是十分有意义的,但需时间的检验。作为一名艺术家,强烈地关注作品的情感表达,是篆刻艺术发展的一种纯粹。
“不肯作小家气,始可删除匠手”。大气象非不拘小节,当从小细节提炼,繁锁而得简约,自有大气象。
平正守法,险绝取势,神韵造境,三者不可偏执。
篆字择字最难在统一协调,有不少印家有“字不配者不刻”是言,可见这种“配”是一种能力,充分展示印家的空间感觉。
治印见刀者形也,见笔者质也,得刀笔者始可论印。
刀感,运刀时瞬间发力留下之痕迹。行刀有往复、修改,同向复刀、局部修改仍以瞬间发力行之,刀感不失。古钅尔、汉印中有刀感、蚀感,蚀感注重自然剥蚀,有收敛意,为金石气之一种表达。若不能用瞬间发力之法,其线条或简单、苍白或外露、直挺,缺少内涵,刀感和蚀感也失去意义。
白文印当朱文印来做,朱文印当白文印来观照,即计白当黑之别论。
刻印家以才情胜者多于运刀之时,随刻治而变,不囿成见,得机趣,让人玩味,颇多合书斋清供。
做残要用自然之法做自然之态,要用做作之法做自然之工。自然之法有二,用刻之法复以刻之,其间产生的虚与残,既自然且有质感和力度;用撞击、敲打、磕碰、磨砂等法,使印面有岁月痕迹,自然剥蚀之化工,苍茫古朴之气出焉。用剥、削、磨、砂、刮等做作手段,均是在印面上做;也可在铃盖时,虚垫、凸垫局部,或用粗纸、网纹纸垫底等做作,不拘一格,合自然之工,表现异彩纷呈。
松而留,开而收,自如生妙;凝重而不滞;生拙而不离,印之三昧可问。
在使用金文字时,常有缺字,若通假不便,便以小篆代之,这种方法很便通,印人常用此法。
疏,舒也,宕,展也。疏宕,舒展,乃小篆结字之要求。上紧身下疏足俊美之态,有飘逸之感受。若足部一旦臃促,则失之坠也。
峭,造险也;古峭,险不外露,险过而方知险也。
布印要统一,讲“气不散”、“气要遒”。正如曹子桓所说:“文章以气为主”,当然印也以气为行。“气不散”是指,方寸之间有一股流动不息的循环之气息,相互间有一种亲和关系,生生不绝,此为生气,不障不碍,故气不散。若空间不配,呼应失调,轻重不宜,破坏亲和,气则散不聚。“气益遒”是指,见刀者凌利不羁,气外泄,伤气;见笔者韵致流溢,气内敛,遒劲,气充言雄。
巧者,心之趣,随手而出。趣多而味不足,则得此失彼。巧者,心之灵,触之则生,欲收不能,若泉涌不竭。施巧不为巧,为之灵;拙中生巧,巧中藏拙,乃大巧是也。
苍茫大气下运刀要注意节奏,构成夸张里当有收敛配合,拘束处勿使人眉头不展,灵动藏于磅礴之中。
大写意印章视觉冲击力极强,利用了视觉设计多种元素,有效延续阅读时间,增强注意力。
运刀过程中没有快慢节奏,光靠线条的组合形成节奏,作品就会少一个层次,线质的表现也有缺陷。除了节奏外,线质的含蓄也很重要,这在古代印章中表现尤为明显。凿印与铸印的线质的细微差别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感受。在创作中,尝试在“凿”与“铸”之间搭建一个桥梁,表现出线质的朦胧美。
治印,见刀者性情也,见笔者修养也,刀笔相融者当为印儒,弗匠手所能窥。
五
古代印章的艺术性在于历史性,站在“石印章时代”艺术基点来观照“铜印章时代”的历史性和艺术性,“铜印章时代”是我们篆刻创作的根源和源泉,而“石印章时代”是使我们走进艺术殿堂的节点,开拓性创作的精神家园。这个即清晰而又模糊的两个时代,都是很清楚用“印材”来划分,时代就这么简单直接,没有隐蔽性,研究印材就看到印章艺术研究的新界面和生命力,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审视印章(篆刻)艺术的视角,印章(篆刻)的研究与赏析不再是印与款的话语了。
印材使用范围,从金属、石、角骨、竹木,到胡桃壳、瓜蒂等,尽可能涉及各种印材,其中一部分纯属印家的猎奇、玩趣、游戏行为,从而丰富了印材和奇特的表现手法,这方面历代印家都有所为。
2007年12月于大研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