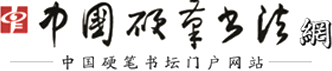在一片长满灌木的山坡的南边,挨着山道有一棵不大不小的老树,一个雨夜被雷火给劈了。伤残的老干在挣扎了两年之后,终于枯死了。这段景象从童年到青年不断出现在我的梦里。经人点拨,我相信这树是我的前身。
我生辰八字中有三个木、两个土、两个金、一个水,缺火。据相士说这八字晦涩不明朗,或为乞丐或成财主。命中多木的人心灵手巧,能文不武,并说这命相做五金活儿好。我说我正摆弄着一把小刀子,那瞎子说:有吃的。后来,又遇一个相士,他仔细掐了八字,要我凑近他,摸了摸我的脸,因为他也是瞎子。突然间他大声说话,像发表申明,说我是文学之士,这辈子他才发现两个,日后在文坛有大名声,为了表示此言铁板钉钉,他起身向我作揖并谢绝礼金。我那时正读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听了自然开心兴奋。
相士有时胡言乱语,自不必当真。但五行有缺失的人,一般都命运多舛,或性情古怪,却好像不假。每有朋友说我不易接近,起先不理解,像我这样平易近人如老媪、乐天开朗的人,如何给人有距离感。后来细细检讨,才发现自己有择人说话的毛病,不是与所有的人都能相处的。于是我断定,凡与我交好的,他八字必须有火,问过几个朋友都无例外。而这于异性好像更敏感,如果八字不谐,不管多漂亮,生理没有反应。
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数比文好,只是偶尔会患口吃,不敢举手发言。我与同学关系不坏,曾经有拉帮当头的威信。只有一回被老师叫到教务处,有一个穿蓝衫细高个的女教师瞄了我一眼,对同事说:“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这话困扰了我半辈子,不是因为受了侮辱,是它提醒我的长相不顺眼。我因此自卑直到50岁,明白没有机会再去追女孩子了,才抬眼自然了起来。
16岁那年,一场国家的劫难席卷整个大地。不久我就发现很奇怪:几乎所有的人都衷心追随并捍卫着一个伟人,却分帮结派然后大打出手。我觉得太无聊也太残酷,就躲进图书馆翻阅文史类的书籍。有一天查阅《辞源》,一条“红羊劫”的词目闯入眼球,纸上赫然写着:“红羊劫指国难。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是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云云。而1966年正是丙午,这好像不是巧合,分明是国家的“八字”!此后我更加发疯似地读各种允许借阅的书,甚至包括养蜂及园林科技的书,但好景不长,图书馆还是关门了。
重新拾起毛笔临帖、作画,实在是精力旺盛而又无事可做的最末等的选择。因此还总与父亲怄气,父亲要我参加运动,不能居家当逍遥派。他早年加入国民党,后来自然不得志,但他希望孩子要跟紧形势,有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话挂在嘴边训人。我笑话他糊涂,窃以屈原的典故自号“醒斋”,后来还求陈子奋先生以此刻印,先生说了,“孩子家清醒的,不必自标榜。”醒斋从此灰溜溜作罢。
为了书画,我径自登门拜访福州最好的几个书画家,起初他们谨慎应酬我,后来经过考验或测试,才都接纳了我。此间有三位老师影响我至深:一位影响我人生观的老师名谢义耕,一位提高我文字能力的老师名何敦仁,而指导我学艺方向的老师是陈子奋。多年之后,我在福州办了个人书画展,此时三位老人都已谢世,我在展览前言里套用当时一句颇流行的话说:“假如没有这三位老师,也许我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想来,因为有那场“史无前例”,我才会读到“红羊劫”,才会“醒斋”,才会学艺遇明师。如果按正常步骤,即使鬼使神差地进了某所著名艺术院校,我估计也未必会学到什么。看看潘天寿当年的研究生,如今不还在摸索吗?当然,所有这些更非相士掐“八字”可以算出来的。
“史无前例”结束后的第20年,我迁居北京,在遇到第一场大雪的时候,我忽然记起子奋先生30年前劝我的话,他说学艺不妙,搞不好将来要饿死在雪地上。我当时暗笑,福州从来没有见到天地白茫茫的时候。现在我走进花园的大院子,迎着大片大片扑面的雪花,用脚踏出自己的路,并没有感觉饿。我对身旁的茜茜说,我平生怕雷,却异常喜欢雪,因为雪与雷,字相似而永远没有联系。茜茜不明白我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