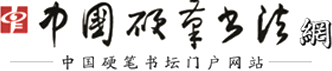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保利藏金》铭文书法说略 丛文俊 彭砺志
纯装饰化文字(辛)
线条化文字(眉)
面块装饰与线性组合(夷)
近年来,中国保利集团公司为抢救保护祖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惜重金大规模从海外购回流失文物,一大批孤品精品得以重归故里,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保利藏金》正、续二编〔1〕就荟萃了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购藏有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主要精品,其中多数带有铭文。这些金文不仅是研究先秦秦汉历史和古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探寻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源流难得的图像文献。由于它们多数为首次面世,以前亦未见于其他著录,书学界对其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在此我们从书法发展史角度对这些金文的书法意义加以介绍和分析,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大体来说,保利藏金的铭文书法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金文前后自成系统,从商周至西汉,全面展现了青铜文明的兴衰史,集中反映了金文由仿形发展至篆引最后至篆隶兼容状态演变的全过程;二是藏金中王室与诸候作器平分秋色,铸铭刻款错金一应俱全,加之地域分布广阔,书法风格表现得丰富多彩。三是铭文以商周时期的小品居多,长款铭文作器也占一定数量。著名者如戎生编钟有154字铭文,字随器形,堪称金文榜书。而2002年新入驻该馆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的(音遂)公,铭文也有98字,其书法美感较我们熟知的散盘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目前在海内外数万件青铜器中,上百字的铭文也不过100多件,因此,这些铭文对于书法研习者来说,弥足珍贵。 金文最早见于商代中后期,与目前所知的甲骨文属同期或略早。保利所藏亘的单字铭文,研究者认为是商中期或以前的作器。必须指出的是,金文相对于同一时期出现的甲骨契刻,是同一文字体系的两种不同表现式样,只有正体和俗体的差异,而没有书体上前后相承的父子关系。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多数铭文较甲骨文更真实地保存了毛笔书写用笔的一些特点,书写风格较为丰富。所以我们把商周金文与秦汉石刻的书法艺术价值相提并论,亦不为过。 保利所藏早期铭文,内容比较简略,大多为族名、先公先王的庙号和人名,文字具有浓厚的图形化装饰意味。这一方面反映了早期文字依类象形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青铜器纹饰的装饰性特点,极尽夸饰之能事,以体现狞厉之美和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朴素情感。所以,笔者在早年的先秦书法史研究中曾将弥漫于商周之际金文书法中这一装饰化制作现象,称之为“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书法美”。
《保利藏金》收录商代晚期的父庚方鼎,内壁铭文将族氏与记事分铸二处,书写性与装饰感一目了然,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族名文字与记事性铭文二者不同的功用。 装饰化与书写性的美感表现不同,但二者相互影响,济成厥美。装饰化强调聚墨成形,装饰为体,工艺为美,而线条化则要求变团块体面为线性笔划,简约流动,以体现自然书写的挥运之理。保利艺术馆收藏的早期钟鼎铭文依装饰与用笔的不同,表现为三种形态:
一是非线条块面装饰的文字,如兽面纹觚圈足内壁上铸有一似“辛”字的阳文(图1.1),字形用圆、方、角块面形体,几乎不用任何线条,修饰颇为繁缛。此虽无关书法,但却对金文用笔发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线条化文字,如同是阳文族名的眉鼎(图1.2),“眉”字完全用线条构成,宛转流动,自由抒展,似乎是用国画的线描手法绘出的眉毛和眼睛,准确地传达了毛笔的书写性特征,揭开了金文书法的辉煌篇章。但遗憾的是,在商周之际的金文中,线性用笔并不纯粹,多数经过不同程度的修饰和制作,所以,线性笔法与块面仿形的结合为本期最流行的第三种表现形式。这正如夷觚上的族名(图1.3),在粗细匀一线条中还杂有圆形与三角形的填实用笔。 金文书体的演进和风格的变化,是伴随着线条化的历程,在毛笔书写感的一步步强化和积淀之下,“质之代兴,妍因俗易”,最后才完成了其功能性的转变。铭文作为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先用笔翻写在坯范上,后再经过若干特殊的工艺手段显现在器身上,因此,书写性是金文艺术发展的原动力,有意味的线条当为其艺术表现的主要形式。保利藏器铭文朝代前后衔接紧密,我们正可以藉此来集中考察金文笔法与线条的变迁,寻绎金文笔法演变成熟的踪迹。 藏器铭文所见早期笔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形如枣核,尖锐中丰。这在前举眉鼎铭文中已初见端倪,是当时毛笔弹性的自然流露。中肥而首尾出锋的用笔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表现为二种变化形式:一种是头粗尾细呈纺缍状,一种是前细后粗并略带波磔的捺笔,此外还有一种肥肚状横画饰笔。〔2〕以上三种形式在商周之际的金文中颇为常见。如周初簋中(图2.1.1),起笔收笔处几乎都采用露锋尖入平出,其中“父乙”二字笔画浑厚,中间肥粗首尾出尖,形成自然的纺缍状。在皇鼎中(图2.1.2),“彝”字左右收笔兼有波磔之势,“皇” 末笔呈肥肚饰笔的用笔特征。这种中间肥硕而首尾出锋的用笔融合了书写与装饰双重功效,也是当时毛笔弹性在书写中的真实流露。在洛阳出土的西周早期簋底墨书“白懋父”中就有这种用笔(图2.1.3)。 早期铭文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起止不露锋芒,藏锋蓄势,有类玉的圆浑之体。如侯尊(图2.2.2),三字用笔中锋紧裹,圆转内敛,线条粗壮匀一,为西周中期后所流行玉箸体的滥觞。这种笔画粗细匀一的用笔在洛阳戈题铭墨书“叔父”也有所体现(图2.2.1),它比尖锋肥腹的笔法甚至还出现得早,但在西周中期以前并不纯粹。两种用笔在早期铭文当中常交织在一起,如父庚方鼎就同时具有这两种笔法特点(图2.2.3)。 如前所述,早期铭文中,装饰性和书写感二者相辅相成。在虔敬心理驱动下,夸饰刻画经常阑入用笔,如子觚铭文(图2.3.1),人名“子”二字,通体被修描得丰腴齐整,只是收笔处渐细尖收流露出用笔的痕迹。应该说,早期修描工艺和填实化体面的用笔特征质重力厚,和同期质朴、雄浑和奇古的艺术风格互为表里。 修饰化用笔不仅在商周之际金文中普遍存在,且不绝如缕,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甚至更远。它从带有宗教化情结的观念转化为真正具有书法审美意义团块形式的用笔,改变了单一的篆引化对用笔和结体的束缚,至今还是一些篆书书家创新所用的笔法之一。在保利新藏西周中期之(音遂)公铭文中,“天”字就还存有早期的块面笔法。 当然,装饰化对金文的影响不止乎用笔,还渗透在整体章法之中。在伯卣中(2.3.2),铭文之外,围饰以“亚”字形边栏,强化上下之间的贯气,加之双行排列,酷似后世的对联形制。这一章法上的装饰在商周之际的其他形器上也能见到。东周时期,错金银工艺流行,铸刻铭文经过错金银装饰,历经二千余年后仍焕然一新。如保利藏战国时期的音律铭文剑,即是错金工艺。不过,该项工艺只影响金文的肌理,不对书体的产生影响。
金文线条化在成熟之前要克服来自两方面的阻力:
一是要挣脱块面仿形用笔对书写性的破坏。把以前的块面改造成新型的线结构,这一变化在金文初期就已开始。如西周早期的仲卣铭铭文中(图3.1),“阝” 部件,面线两写。在木羊簋甲乙二拓片中,同一部件二者书写就完全不同,乙器用块面,而甲器则将块面改写为圆转封闭性线条(图3.2)。这种用线条改造块面是金文线条化必由之路。
二是要规范仿形线条所造成的结体上的自由化。初期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多数字有数种甚至数十种写法,仿形线条平面排列位置的不同也给整体性章法带来影响,大小错杂排列差异辄至数倍,这种仿形线在西周中期也还继续存在。如弦纹垂腹鼎(图4.1),器内铭文2行5字,从右向左纵向排为二列,首尾二字为求穷形尽象,分别所占空间几与其他三字相埒,加之转折方硬,从用笔到结体,明显受到甲骨文的影响。还有仲卣铭文(图3.1),其中“彝”字结体极尽夸张。这种看似生动而实则坐实的文字,在今天看来,其大小对比虽然也体现了古人原始书写美感,但随体诘屈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笔顺之间的关联秩序,与“以趣约易”书写性简化原理格格不入,不能代表西周金文的主流。
当书写化线条从指示性向符号性转化的同时,金文线条的质感量感的提升自然要求结体的规范化。在西周中期以后,当礼器脱去神秘的外衣,铭文成为关注的对象时,篆引化法则是人们共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 篆书线条,孙过庭《书谱》曾概括为“婉而通”,即要求匀称圆转遒美,结连贯通。笔者曾从书体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将大篆的本质特征归之为“篆引”,〔3〕已为书学界所广泛接受。在我看来,“篆”代表萦绕叠和屈曲圆转的特征,包括线条的曲直、粗细、长短及排列组合;“引”代表书写上的转引仿形、中含内敛、力气长之类的用笔。金文篆书在“篆引”动力之下,大致经历了由面仿形到线仿形最后定格为具有婉而通线条的篆书。一般说来,笔划粗细均匀在周初铭文偶能见到,如周初的从簋(图5),通篇线条匀称,没有同期多数铭文的块面和仿形用笔,它虽然代表了金文字体的发展趋势,但其质感与后期的玉篆引的用笔特征还并不完全等同。〔4〕后者是随着铭文内容日益增多、字形渐趋固定之后,在西周中期后金文中才大放光彩的。 西周中期的铭文,文字常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形,这表明书作者的章法意识已经觉醒。用笔上,基本脱去了块面笔法,克服了仿形线条对结体规范的破坏,起收笔处的提按动作消失,前期和甲骨相类的直线圭角也被盘纡圆转所代替。起迄藏锋的笔法虽有些单一,但线条化的质感程度无疑有所提高。如本期的有盖叔丰簋,其乙簋器铭(图6.1),虽大小不一,但书写自如,布局上趋于匀整统一;而甲簋铭文(图6.2),字形整饬,线条愈加圆润,字距行距益为匀整。保利藏器中还有一件同人所作铭文大致相同的无盖叔丰簋(图6.3),整体章法的组合似不甚连贯,但单个字的线条却中含内敛,力气长。
在保利所藏所有青铜器铭文中,有被专家称为“金文之最”的(音遂)公(图7),它铸有98字的长篇铭文,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5〕这件公上的铭文与以往所发现的纪名、纪事类青铜铭文体例、格式截然不同,却与现存的《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所以,重文字数少,绝对字数多。从书法风格来看,与散盘铭文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笔画短促曲美,字形欹侧错落,比散盘铭文稍显松驰的结体要凝炼紧凑。开篇首行前几字,字形偏小,略显拘谨,愈往后愈显得轻松自由,铭文末尾一行因字数少,有意大字书写并拉开距离,可谓匠心独运。 “王作左守鼎”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周王自作祭祀鼎,铭文“王作彝左守” (图8.1),清楚地交待了这是周王制作的祭祀用的宝器,属最高级别的礼器。此鼎的时代研究者定为夷王时期,为西周中期偏晚。王氏作姜簋(图8.2),是周王为后妃作器,年代属夷王、厉王之际,可见,二器的时代基本相同。在书风上,前者结体比后者整饬,后者用笔较前者浑朴。二铭文排列整齐,间距疏朗,形体狭长一如熟知的毛公鼎。左守鼎中 “王”之“丨”划,“守”的“宀”头,下部线条端直拉长,其篆引化特征已肇秦世小篆书的前声,体现了礼乐制度之下的秩序感,与意涉魂奇的商周风格绝不相类。 周王作器是王室作器铭文的代表,多庙堂之气,它是当时书法的正体。从书写者的身份来看,《礼记?曲礼》有“史载笔”之说,据《周礼?春官宗伯》“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达书名于四方”。其他如大史、小史等职掌均与文书有关。所以,王国维认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6〕目前所见金文中,史官铭文材料多达一百十余条,〔7〕这些不同名称的史职可能就是这些金文的主要书写者群体,即后世所称的书法家。以周王室作器为标尺,去对照同期其他铭文,便会发现铭文书法也有王室与诸侯、京畿与周边书风的差异。 应国,为地处今平顶山一带周代诸候国,传世铜器较多,仅保利就藏有五六件之多。恭王时期,曾对该侯国见工进行赏赐,馆存的见工簋、见工钟铭文(图9.1~9.2)记录了此事。二器文字规范,结体平正,用笔圆融,线条平直硬朗,体现了书写者严守法度的心态。应侯盘(图9.3),起止处多呈钝锋,线条饱满匀称,风格雍容典雅,较周王器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文书风这种上下趋同现象,和西周诸侯国的构成直接有关。西周分封诸侯国,统治者多来自王朝,诸侯之史自然也会因袭周室之史书写金文的一些基本笔法。
一般来说,同一家族数代连续作器中,铭文书写有相对稳定的传承系统。前举木羊簋,器主木羊与我们熟知西周微氏墙盘属于同族,所祀父乙,为昭王朝代的第三世(墙盘为第六世)。其铭文书风与这一时期所出的其他形器如丰爵、析如出一辙,如“羊”字写法均为中间一横,下作三角形。但应国所出的簋(图9.4),其书风似与同期其他铭文有所不同。文字奇古,行气左右摇摆,每行首末严重高低错落。从内容上讲,此簋记述了周王来卫国的姑城,他没有忘记应国的公室,赞美并赐给朋贝马匹,为此作簋祭祀其祖先。显然,这是公室主人(见工之父)在称侯之前所作,根据器主不同的级别由不同的人所书写的习惯,该铭文的书写者可能为卿大夫之史,与应国侯器出于不同的书者之手。 立免形典尊(图10),记录了王命小臣丰赏赐给名叫典的人(正弓用的器具)。结体草率纵逸,大小错落有致,小臣在西周“掌王之小命”,此铭文或出自小臣笔下,亦未可知。 有盖氏簋(图11),盖器铭文书写均左起右行,一改西周书写之制。用笔纤细,一如甲骨契刻。字形狭长,为取纵势,有的字如“纟”旁,回环多至四次。此当或为与商朝有关系的地方性铭文书写风格的延续。 戎生编钟(图12),在保利藏器中铭文最长,字形最大,字数也最多。
内容上看,其时代不出懿王至厉王之间,从风格上来看,有明显的晋国地域特征。文字之间大小错落,上下多取纵势,结体自由,左右腾挪。从字形上看,多有不同于西周中后期金文的简率写法,与东周时期铭文书体有相似之处,体现了作者有意创新的意识。所以,有学者认为“撰作、书写戎生的人,大概具有不为传统所束缚的特点,所以在文章和字形两方面都采用了一些当时一般撰写铜器铭文的人所不用的较新的写法。”〔8〕 保利所藏西周中后期青铜铭文中,有不少为同一人所作,器形不同,但铭文完全或基本相同。此虽为一人一时所写,但极少有完全相同的字形和章法。前引保利所藏的二套叔丰簋,四处铭文无一有完全相同者。白敢(qi)一对(图13.1.1~13.1.2),盖器四处铭文亦各有特点。
总体来看,盖铭容与徘徊,疏密有致,而器铭则各尽其势,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虎叔作姒簋(图13.2),器铭相较于盖铭文字,多数为反书,金文的“正反无别”被书者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受制作工艺或布局空间所致差异,虽非书写者有意识的追求,但还是掩饰不住书写者创造的天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风格呈多元化的局面。这既有因诸候异政所带来的时代风气的变化,也有因南北地域差别形成的风格差异,更有因为写刻的工艺不同而造成的书体的不同。 益余敦(图14),为春秋中晚期作品,是以邵穆公的远孙益余和他的妻子陈叔妫二人名义所制。除字形的时代差别之外,用笔上对以西周时期的金文玉箸线条的美感特征有所破坏,线条已没有西周金文书法的浑穆厚重,但却纤而不弱,瘦而不枯,加之章法上松下密,前密后疏的变化,更显得摇曳多姿。 如果说铸铭线条圆浑凝练,那么,刻铭则笔锋清晰,写味十足。春秋时的工(wP)大(zP)矢与战国铍二兵器铭文(图15~16),一铸一刻,前者笔画粗细匀一,多直线条,明显是用笔将就书体;后者因势出体,变方折为弧曲,钉头鼠尾,起迄历历,笔势与体势圆融一贯,与包山汉简相似。
来源: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