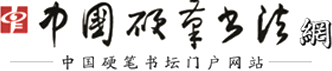传统就是生、活 格式 于明诠
格式 本名王太勇,1965年生于山东阳谷县。中间代诗人,评论家。
于明诠 别署于明泉、于是乎等,男,1963年生,山东乐陵人,现供职于山东政法学院,任哲学副教授。系山东书协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沧浪书社社员,山东艺术学院特聘书法硕士研究生导师。
格式:在这个价值失范、心灵失序、物质失度的时代,谈论传统,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在拨乱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是一种不断生成的东西;而在反正的层面,我们又体察到传统充满着相当左右逢源的质素。作为“流行书风”的代表书家之一,你参与了中国当代书法界的多次论战。在那么急切而又真切地辨识与求证中,你肯定有话要说。
于明诠:“拨乱反正”这个词值得玩味。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个词大概都会有一种悲欣交集的感受。历史每向前推进一步,似乎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拨”、“反”的力量在动作着。读中学时,见到胡适博士的话——“历史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感到义愤填膺,怎么能如此践踏历史、践踏人们的历史感呢?现在想想,胡博士所说的恰恰是一种客观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一种无奈。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今天似乎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传统当然不是历史,但传统是在历史烟尘中发酵生成的,是在历史的一头雾水中泡大的。今天谈传统,我们总是会联想到另一个概念——经典。经典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经典就是传统与文化的标本。由于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与文化背景下凝固而成的,它所发出的古暗的幽光,除了象征时空的遥远之外,还让人们体味着一种欲抛难抛且又欲近难近的无助与无奈。就像一件汉罐、一件宋瓷,或一幅明清字画,除了点缀我们的生活,满足人们的崇古癖好之外,还有什么呢?扔不得也用不得,只好这么供着。有人说是欣赏其艺术,这很令人生疑,欣赏其旧还是欣赏其美?美与旧是必然的关系吗?当然不是。因此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过就是一种时过境迁之后的浮想联翩罢了。传统,说白了就是对经典的重复误读。不过这种“误读”,总是以“拨乱反正”的面目出现。面对经典标本,有些人总是企图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以完成他们替天行道、化育民众的使命,另有一些人却相反,沉湎于从共性中寻绎个性,以实现自己创造的快乐。无疑,前者是道学家、学问家,而后者是艺术家、创作家。两者对传统的介入方式如此相异,但却都是建立在个人体验或时代局限内的“误读”。
书法是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她在今天的状况如何,对整个文化乃至今天社会的影响不大但也不小,对其中某些现象的思考或许也能折射出这种“误读”的丰富的差异性。关于“流行书风”的论辩就是一例。滑稽的是,反对者以凝固的标本——“经典”去置换演进漫流中的“传统”,其实质是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来对“误读”必然性予以拒绝。这是不能容忍的。批评可以是另一种“误读”,但不能“不许误读”。传统是什么?是“生”与“活”,是由“生”而“活”,是因“活”而又“生”。画家石鲁这样解释传统,前人创造的好,流传到今天,就是传统,而我们创造的好,流传到以后,也是传统。画家的语言朴实,却也准确。反对“流行书风”的论调貌似只有他们才尊重传统,事实上是他们想剥夺传统“生”与“活”的权利。
格式:传统不是历史,却是历史的产物。这说明你的误读,既有主体的生气,又有本体的活力。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传统往往是正统或者本分的代名词,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他们常常以为“一”没有传统,而“二”是有传统的。这种线性的进化论观点,一方面酿成了他们的抱残守缺,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忽略了传统的整合功能。传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是我们不断面临的起点。这个起点,不是从零到零的重复,更不是从一到一的循环,而是对各种异端的及时总结。庞德说,只有异端,才构成历史。我认为,异端是传统的一种活性素,或者说传统的活体存在就是异端。
于明诠:没有丰富多彩的“误读”,哪来的“整合”,或者说“整合”什么?而没有这种不断“整合”,仅有“复制”,传统还将存在吗?孔子的儒学经典若无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及陆、王等人的不断“误读”与“整合”,当然不会有儒学的传统。传统不是一种“本源性存在”,而是在它的不断变异甚至不断被颠覆之后的演绎与整合,也就是你前边所说的“拨乱反正”,在这个意义上说,拨“正”反“乱”也是一样的。艺术创作常常标榜“原创”,细想起来,不折不扣的“原创”有吗?没有。只是相对所谓“正统”来说罢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旦被推为正统的东西,差不多在人类文明发展中都不起什么积极作用。庞德的说法,是艺术家有感而发的感叹,但这应该成为一个常识。昆德拉说得似乎更到位——让我接受的都不是好的,只有能够动摇我的,才是好的。
就书法而言,你说王羲之是“一”还是“二”呢?就其原创意义来看,它是两汉正统书风的异端,他曾经被人讥笑为“野鹜”,而相对晋唐以来的流风所言,则又成了人们膜拜的正统。其实,它既不是异端也不是正统,异端与正统是后人“误读”的结果。在中国书法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自王羲之之后1600年行草书风的漫流嬗递其实恰恰是“异端纷起”的延续,颠张醉素、颜柳欧赵、徐渭八大、王铎傅山,他们无不以其独具的个性不断地颠覆着我们关于二王书风固有范式的印象,开拓出传统的新生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传统再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所以,你提出的“异端是传统的一种活性因素”,“或者说传统的活体存在就是异端”,这观点我完全赞同。当代美术批评家李小山在谈到“意义的生成”时说,意义本身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无意义这个存在前提下,经过抵抗和斗争才产生了意义。而创作永远是一种挑战,没有颠覆性和革命性,它便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然而一旦它作为意义的载体而存在,就表明它的存在价值已经获得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整合就是异端的创造。
格式:异端之异,与误读之“误”、整合之“整”密切相关。当然,这绝非一日之功。我曾记得有人讲过慢功出巧匠,没听人说过慢活出传统。在当下,速度似乎成了统化万事万物的法宝,而中国艺术的几大国粹,又仿佛全是慢的产物。传统果真是慢的吗?如果不是慢,那么传统内在调息的节律,又该如何把握?里尔克诗云,“你内心的优雅,使骨头开出血肉。”传统的内生性与自生性,又该如何区别?二者是否构成了传统节律的基础性元素?
于明诠:应该说,传统自在的调息节律源于历史本体的调息节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读一读这传诵千年的句子,我们就无法摆脱历史厚重感的笼罩。所以,我宁可认为,“慢”,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属于传统自在的调息节律的固有品格。“朝如青丝暮成雪”,“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快还是慢?“思接千载”,“精鹜八极”是快还是慢?其实,传统的内在调息节律中既有“二黄慢板”,也有“西皮流水”。你所说的中国艺术的几大国粹似乎全是慢的产物,我不知你是指艺术家的修为过程还是艺术创作的单位时限,倘是后者,其实无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这里,我们说的“传统”也已经误读成了“古典”的另一个术语了。倘是前者呢?我的理解是,慢是一种“不急”,或说“悠然”,是一种心态。心态对艺术创作很重要,古今都是一样的。传统艺术的修为,既强调“面壁十年”,也强调“横超直入”。传统的内生性并非自我封闭,而是“境由心造”那样的自由与广远,从庄子“心斋”到孟子“浩然之气”,再到陆九渊的“吾心即宇宙”,莫不如此。传统的自生性呢?也不能简单化为某种惯性,而是老子的“道生一”与“三生万物”,从石涛和尚的“一画”说到计白当黑、墨分五色,再到中国书画三笔两笔便是一个宇宙乾坤,这种传统的振拔与漫流何其逍遥何其壮阔!里尔克的这句诗我也好像读过,它表明传统真是不应有国界和民族区分的,或者说不同民族间的传统又有着许多相似与共通之处,写得真好,“内心的优雅”不就是一种传统的力量么?“开出血肉!”——你看这种力量又是多么鲜活灿烂!
格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古人的这句话,既指认了传统的开阔与宏远,又提示了传统的始发与建元。实际上,任何一种话语生产,都不会没有进入社会实践的功利目的。传统从字面讲就是传和统。传是传播,统是整合。传统作为一个强大的话语生产系统,其在当下形形色色的话语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有效性,盖源于此。传统不是种子,因为它的生产和消费都不是一次性的。它可能是基因,因为它既能遗传又能变异。以往人们看待一种传统的有效性,过多地把视线纠缠在遗传上,而很少把变异视作是传统展开的过程,以致于闹出不少陈陈相因的笑话。
于明诠:传统当然不是种子,而充当种子的只能是传统所孕育生成的蛋——“经典”。但传统的流传,又确实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无限扩张。这一点,我们谁都不能无视它,甚至不管你对它了解多少,它却会主动地找上门来把你“网”进去。所以说传统在当下的有效性,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的。十年文革敲碎了许许多多的唐宋瓷罐,原以为从此可以了断一条传统的脐带,不曾想这些瓷片的碎裂声息,如今倒成了吊我们恋古胃口的馋虫了,若论这种扩张在当下有点变本加厉,倒是源自于对它的那次“革命”。一个世纪之前,《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说:“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国学者何?经史子集是也,王国维概括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亦即文史哲也。这正是传统的文化与学术载体。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离开自己的哲学、文化与历史吗?至于传统的遗传与变异,我以为两者是同样重要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面对传统,我觉得我们常用的“弘扬”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弘扬”是什么呢?是既有继承还要有创造,而继承是遗传创造则是变异。否则的话,若要人为地割断、抛弃、破坏,结果就是前面说的,要么徒劳无功,要么抽刀断水。而简单承袭泥古呢?结果可能就是把鲜活生动的传统变成历史长廊中风干的腊肉,最终只能是因腐烂而消失。
格式:革命者往往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不鲜见,它从另一个向度,彰显了传统自在的反动力量。如果我们置传统的空间性而不顾,大谈特谈传统的时间性,很容易走上一种形而上学之路;如果我们置传统的时间性而不顾,专门特异地讨论传统的空间性,也很容易陷入机械主义的泥坑。过去我们看重的是传统的流传,而不太重视传统的播散;看重的是传统的统一,而不太重视传统的统化,因之传统往往以集体的面目出场。殊不知,传统是由个人创造的。况且它与风气、习惯的关系,与经验、记忆的关系,颇值得我们在今天予以认真追究。
于明诠:哲学上谈时间性,是强调其一维性,而谈空间性,则是强调其广延性。传统总是流传有序,起码表面是这样。但一维的时间性告诉我们,时光不会倒流,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之任何泥古不化的道统观点都只能是刻舟求剑式的虚妄之想,其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孔孟之后汉代出了一个董仲舒,他讲“天不变道亦不变”,结果佛教盛行,这“道”被禅宗、道教重新改造,心外无物了。到宋代二程、朱熹,讲心物一理,而陆、王则干脆强调明心见性,吾心即宇宙了。你说“道”变不变,“天”变不变?正如你所说的,传统往往以“集体面目”出场,我们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截取任何一个横断面皆是如此,但若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比如道德,章太炎就说过,今人看古代的道德近乎野蛮,原因就是“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乎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乎于平民的。”(章太炎《国学概论》)即是从每一个历史断面上来看,我们也要充分看到空间的广延性,从桔生淮南淮北、百里不同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南帖北碑南北二宗,都可折射出传统的丰富多彩性。不仅如此,正如你所说,归根到底,传统是个人所创造的。艺术的创造者是个人,著述立说的当然也是个人,从结果看,传统或可就是“集体无意识”,但集体却是“个人”的集体。但对于个人来说,风气、习惯,甚至经验、记忆,也是传统的载体。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这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待传统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辞海》里的原话。因此说,风气、习惯以及经验、记忆,既是传统播散与统化的物质载体、是温床,也同时是传统衍生的反向作用器,是一种无形的束缚力量。
格式:传统的反作用力,并不表明传统对个人的覆盖,恰恰是个人性的有效复出。古人云,一叶知秋。用全息生物学的观点看,就是片段的包含整体的全部信息。由此我想到一种传播已久的说法,即传统在民间。大量事实证明,传统在其他的地方生长存活的可能性极小。近年来,“民间”一词被一些艺术界以及学界利益之徒搞得面目全非,如今也该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置身民间,你发觉传统的呼吸是那么地自如而坚韧;深入民间,你才觉得尘埃落定或者水落石出,是传统的本然呈现。话又说回来,既然传统在民间,那么它与主流、与历史,就不可能不发生一定的纠葛,甚至这种纠葛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传统生长的一种外力。内外的结合,尽管情形复杂多变,但还是能让我体察到,传统有可能就是集体潜意识在个人的集中体现。
于明诠:提到“民间”这个词,总能让人产生许多疑问,与“民间”相对的是什么?是官方、贵族?而在古代,贵族与官方是一体的,并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陶渊明去悠然见南山,说明他由官方转向民间了。今天呢?有官方却没有贵族,你可以说有富人,但富人不是贵族;你可以说有知识阶层,但知识阶层不是“士”,“士”是在社会道德良心上有担当的,今天的知识阶层中有相当一些人自以为自己是“士”但却少有社会担当。因此,我说这些人是“伪贵族”,他们最喜欢与民间对立。“伪贵族”虽然“伪”,但一旦跳了“贵族”龙门,是绝不效法陶渊明去“悠然见南山”的。近年来,在书坛上有一些教授、学者以经典来否定民间,说白了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卑琐的心态,生怕沾染了一点民间气味而破坏了他们用虚头衔堆砌而成的“高贵血统”。我不知道,若离开民间是否还存在不存在官方和所谓贵族。若离开民间我不知道传统之根将植于何处。一位作家若离开民间将怎样写作?一位画家若不深入民间写生如何画画?一位音乐家若不深入民间采风怎样谱写旋律?连封建皇帝都承认“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今天那些“贵族”艺术家与理论家怎么就断然否认呢?去年上海《书法》杂志第五期刊发过我的一篇文章——《经典临摹与民间采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书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翻看。当下,各种传统文化艺术形式都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问题,而唯有书法艺术是其中最后一件欲脱未脱的长衫,所以,你所说的“传统在民间”这一传播已久的说法,对当今的书坛来说,可能还十分新鲜,所以我的观点也必然性地遭遇到书坛“伪贵族”们的不解与批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书法经典与其他文化艺术经典一样,都是源于民间甚至是直接来源于民间的,青铜甲骨秦砖汉瓦不是民间吗?作为诗人,你总不会否认《诗经》与《古诗十九首》的民间性吧?但那是最经典的经典。至于主流问题,则是指艺术创造初始时期的表面境况,随着历史的推移,自封和他封的所谓“主流”往往过后并不算数,当年康熙、乾隆在宫廷里大倡赵、董主流书风的时候,扬州八怪却在偏远的民间街巷热火朝天地做着颠覆性的艺术创造,他们与权重位显的张照、何焯等主流书家的主流书风之间的差异是社会体制造成的差异。至于今天,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主流非主流问题,我更愿意从艺术家、理论家的艺术良知与学术品格上去关注。
格式:的确如此,对主流的认定牵涉到艺术品、理论家的艺术良知与学术品格,遗憾的是这个前提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并且这种忽略与艺术无关。就艺术而言,我以为传统是一种自决,这里面当然包含着选择与决断两个层面。据我所知,你在从事书法创作的同时,还从事绘画、京剧、诗歌等诸多艺术门类的研究。这种旁通,一方面提升了你对中国书法的认知;另一方面又为个人的书写输送了大量新鲜的基质。不同的选择与决断,反复的选择与决断,造就了你的执著,同时又为你的个人性在类的同步呈现中擦拭出鲜明的色彩。你不会否认这与传统的砥砺有关吧。
于明诠:面对传统的选择与决断,既取决于公共的时代性、社会性,也有着必然的个人性。这种个人性可以理解为兴趣、爱好,甚至偏狭与癖好。但融入的深度与磨砺的向度,却更多的来自个人的执著与坚守程度。我在20年前大学时读的是政治专业,后来做过12年党校教师,现在一所高校教哲学课,书法、诗歌、绘画、京剧都是我的业余爱好,当然,研究与旁通还远远谈不上。然而,虽是业余,但对于今天的我自己来说,尤其书法,它却占用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京剧不说,我绘画与诗歌的风格样式也都是很古典的那一类,通俗的说法就是“挺传统的”,至于我对书法的理解与探求也自然属于这样一类风格,这大概是缘于“我”个人的偏好,我坚信,融入传统的深刻程度与创造的高度总是一致的。或如你所说的——“与传统的砥砺有关”。而当我常常为某些作品线条点画的不到位、“不传统”而感叹的时候,自己却被划入“流行书风”而成了“不传统”了,这真是一种讽刺。由此我想到诗人韩东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对的,那么他们就是错的;如果他们的写作是对的,那么我们就是错的。有人评论说,当下书坛的“流行书风”之争是不同艺术观念之争,我觉得倒更像一场非艺术观念与艺术观念之争。这里稍作说明——在我看来,“流行书风”是20年来书法艺术发展的传统正果,因此,在伪传统伪贵族充斥书坛的当下,“流行书风”的提法是17年来伪传统书家与伪贵族学者对这一传统正果谩骂而来的(参见拙文《当代书坛创作流派与格局试说》,载《书法》杂志2001年第12期)。“流行”一词切不可作字面理解,正如赵树理的“山药蛋派”不能被理解为一堆土豆、马蒂斯的“野兽派”不能被理解为一群狮子老虎一样。“流行书风”的确如批评谩骂者所言太不名副其实,因为它远未“流行”。近年的书坛流行什么呢?我们到大大小小的展览厅去看看,大流其行的是那些平平庸庸的伪传统伪古典式的“老干部体”,传统经典播下的龙种收获了如此跳蚤,这不仅是书家的悲哀、书坛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说到底是书法的传统在当下的尴尬和悲哀。
来源: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