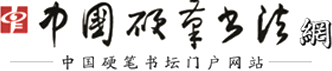杨吉平先生《“智性书写”和贾平凹书法》,—文(见2001年第36期《书法导报》),站在“很高的高度”上,以其少见的“学术魄力”审视了近期兴起书坛的“智性书写”群体。也许,杨先生曾经有过精彩论文,否则他不会获什么奖。但这一回,杨先生却错了,几乎全错了。如谓不信,众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采。
错误之一——主观武断
杨先生在文中说:“对‘智性书写’我认为与当代许多青年书家提出过的口号没有多大差异,或曰大同小异。”又说:“我不知道‘智性书写,的‘智’意义何指,但知道贾平凹先生对‘智性书写’的看法是非常‘智性,。”既然杨先生不知道“智性”的“智”字意义何在,怎么能得出“我认为与当代青年书家提出的口号没有多大差异”的结论呢?“提出过的口号”又是指哪些“口号”呢?看来杨先生对“智性书写”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关于“智性书写”,文艺评论家沈奇先生称其为“未来文化史上的一次文化事件”,因为它是国内理论界与创作界的第一次共谋行动。作为批评,“智性书写”的理论家们不是如同以往那样跟在批评的背后写“总结”;作为创作,“智性书写”的参与书家因有了理论的桥梁而走得更加有力。因此,沈奇又概括“智性书写”为“脱序、重构、板块、呈现”八个字。八字虽少,却道出了“智性书写”的关键,此一吃紧处,限于篇幅木再展开。
错误之二——以偏概全
贾平凹在充分肯定“智性书写”双年展的前提下,也对:智性书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批评。这也就是杨吉平先生文中认为的“非常智性”的看法。但是,杨先生却把此当作贾氏对于“智性书写”双年展的全部意见倾泼给当下书坛,这就不免一叶障目了。杨先生如此行文不禁让我想起1967年北京石油学院“红代会”编选的鲁迅语录一事,他们在文中把1923年鲁迅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片言只语收录进来。鲁迅这几句话只针对当时一个叫钟孟公的人而发,此人对《晨报》开展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满呼吁停发。鲁迅认为钟的言论太旧,劝孙伏园将讨论继续下去。编选者完全不顾这一具体的背景,把鲁迅的话当成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来使用。这几句话是“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里被“揭”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