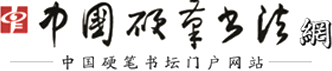在梳理和重新審視皖江文化的工作中,如果疏忽、甚至是視而不見“上掩千古,下開百祀”的鄧石如,皖江文化之說是無其份量可言的。我曾在給一位編寫中國印學史的朋友一封E-mail中說:寫印學史,如果不寫江、浙,只能是一部不完整的印學史;如果不寫安徽,那將不成其爲一部印學史。可見安徽在中國印學史上主宰乾坤的分量。
完白山人鄧石如自是中國書法篆刻史上一顆燦爛的巨星,倘若缺了這顆“偏師爭與憾長城”的巨星,清嘉慶以後的書法篆刻藝術的走向很有可能將隨著當時偏尚帖學和左右書壇的“內閣學士”翁方綱等人的所謂循“六書之旨”、守“古法”和浙派後期印學只肖其貌而不知攝其神、流於形式、繼起無人、漸見衰落而步入不知要摸索多少年的黯淡期,其歷史也將隨著書法篆刻藝術生命的衰竭而改寫,嚴重點說,中國書法篆刻史早在二百年前就該劃上句號了。相信這不是誇大其辭。
要言之,中國書法篆刻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書法篆刻藝術的出新史。鄧石如書法篆刻藝術的傑出成就,不單單表現在他的作品精湛,更重要的在於他的銳意變法和革新實踐完成了對中國書法篆刻藝術的發展作出的“開古來未發之蘊”的重大貢獻。晚清書法篆刻名家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等莫不受其影響而脫胎自立,從而構成嘉慶之後書法篆刻藝術創作活力充沛、氣象日新的繁榮格局。及至現在的書法篆刻藝術的創作依舊遵循著帖學碑學並重、書從印入、印從書出和印外求印這一雖說經歷二百餘年但在今天仍然是有著指導意義的美學理念。康有爲先生的“下開百祀”的預見是何等的高明。
1987年我去西泠印社領獎,當我登上位於美麗的西子湖畔的孤山西泠印社拜竭鄧石如塑像時,我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二百年後的今天,作爲翼圖接步山人書法篆刻藝術也是出生在大龍山下的後生的我,站在印學聖地面對著一代宗師那樸實而又帶著濃郁的龍山鳳水土氣的山人,一股酸楚湧上心頭:
山人,您十七歲以後便長期一笈橫肩,背井離鄉、浪迹天涯;您雖自號“完百山民”卻又“回首肝腸碎”(山人三十二歲時替父到壽縣教書,其弟作《送行》詩中句);您雖藝“撼長城”、標程百代,而那一拐竹杖卻又成了您是“笈遊道人”的特殊標記。您走的是那樣的遠,帶著您的高技大藝;您始終情系故土,在跋山涉水傳播著您的藝術同時還不忘告訴世人,您“家在四靈山水間”、“家在龍山鳳水”(山人自用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