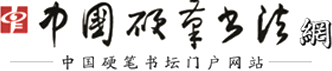已经炒作了一段时间的“流行书风”,虽则不是什么重要的学术问题,但近来书坛上对其进行的批评和反批评却构成了一道让人欣慰又让人无奈的风景线。这集中体现在近期《书法导报》所发周俊杰与王镛的几封公开信上。
书坛都知道,周曾为王写过一万多字的作品集前言,被书坛视为颇具学术价值的个案研究佳作:周还为王之书法被人斥为“假、丑、恶”的代表、直至要“鞭笞”而站出来撰文,为之辩护,可见二人的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而我们感到欣慰的,正是周先生并非因亲朋老友而放弃了原则,他两封致王镛先生的信中对“流行书风”具有高度学术品味和学者风度的批评,使我们感到了一位学人的真诚和高风亮节。这是否预示着人们曾反复呼吁我们这个时代要形成真正书法批评良好学术环境的愿望由此而进入到一个更加令人欣慰的阶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王镛先生的“反批评”。他在复周先生的信中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不正面进行回答和论辩,而是强词夺理地提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企图以此攻倒对方。对事实的歪曲,加之王朔式的文风,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位京华名牌大学教授之手。即使如此,周先生也平心静气地对之进行了一一回答,并再次深入地从学术角度谈了他对当前书坛诸多问题的看法。细细地阅读和品味两人的文章,便可深深地感到,二者的学术水平和人之整个素养,可谓霄壤之别。这里我们再举出一个例子,乃周先生也未发现的问题,从中可领略到王文文风和为人的一斑。
4月10日《书法导报》刊发《王镛答周俊杰先生“万言书”》中有以下一段话:“据我所知,早在15年前即1987年,刘正成先生就在《书法》杂志第五期上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概念,那篇文章的大标题就是《‘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倾向》。”接着以一种洋洋自得且毫不饶人的口吻说:“您可千万别说您从来不看《书法》杂志,而且也没听说过此事。”周先生在《再致王镛先生书》中说:“恕我寡闻,未曾见到。”周先生当然见不到这一文章,因为该期《书法》杂志及创刊二十多年的所有《书法》杂志都从未刊登过刘正成先生的《“新古典主义”的创作倾向》一文,而更为荒唐的事是,刘先生也从未写过这一为王镛所杜撰出的文章。但王镛先生既然白纸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