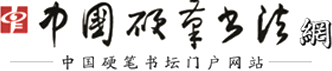小时候画画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爱好。我学画的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条件有限,很难见到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在当时见到的近似于年画的作品教多,大多格调不高。那时我喜欢写意画,特别崇拜、石鲁、蒋兆和、黄胄、石齐等艺术家,后来到了天津美术学院学习,通过写生、创作、观摩古画,随着西方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大量出现,使我对艺术有了新的发现和认知。

我以前一直画写意画,但是我很喜欢工笔。1980年我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原准备考浙江美术学院工笔画研究生,后来听说留校了,又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去。我被留校任教一直继续写意画,创作了《春城无处不飞花》,这幅作品造型上向黄胄先生学习较多,此画后来虽然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奖项,但我清楚自己对艺术的了解还不是很透彻。后来在我师兄的启发下,我开始思考,什么是艺术?在当时我读了很多书去了日本和敦煌考察,慢慢地清理的以前对艺术的看法。随后我参加了美协组织的取太行山的创作班。在那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如何发现美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我在思考以何种方式表现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有内涵的人物。在自己不断研究和同学争论中,我画了《山地》,此时的我已经发现了工笔画的魅力,它可以容纳色彩和其他艺术语言,诸如素描、水彩画、油画等西画语言,表现力度非常强。所以我选择了画工笔画,而且发现它也很适合自己。因为我有耐心、有方向,感觉到在写实的绘画当中没有很宽的领域可以深入探索。我开始把表现人的本质放在了首位,而不再是一种政治功能。《十九秋》人物的原型是在河北,是我二三年的生活积累和体会感受,这个形象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我脑海里长期酝酿的一个单眼皮的中国农村女孩的综合形象。
您的工笔画无论是乡村少女还是城市女孩,给我一种强烈的现代感,透露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朦胧美,它是婉约的也是伤感的,唯美至极。唯美其实就是一种画面意境的超现实的营造,在我看来一个画家的成败最终决定因素在于画家对意境的营造。您在《衡中西以相融》中的思考:“中国画,中国工笔画,其精神意度、方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容纳西画的。”“西画的观察、审视、理解和提炼,和晋唐传统并无二致,可以对应、契合。很多西画作品能直接的给我们实践的参照,这种实实在在的启悟益人神智”。
由于中国画材料的特性,不允许你照着一个真实的素描关系作画,必须要高度的提炼概括,画面中该写实的写实,不该写实的一定要舍弃。中国画是很难用照片代替的,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画的生命力所在。绘画中我们谈意境的时候往往想到山水,其实人本身就有意境,这个意境从何而来?从他的造型上、神态上,从画面的形式上。我们应该向雕塑学习,雕塑没有背景但能表达出人的意境。
写实给予中国人物画,不仅仅是结构、透视、色彩和光影等以科学为基础的造型技术和图像经验。我是从晋唐文化入手,寻找东西文在人文精神和文化规律上的一致性。晋唐绘画中的人文精神以及观察、理解对象的方式和西方并无二。
相遇永恒
在您的工笔画中,每幅作品给人感觉是超越现实的,感觉都是瞬间即逝的感受,它跟自然的真实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您的作品一大特点,您一定有很多体会。
在创作实践中,我常常把偶然易逝的东西扑捉住,我祈求的是,一经相遇,便成永恒。诸如《山地》中老人的脊梁背;《十九秋》少女从红叶后面闪出的偶发情节;《米脂婆姨》瞬间恒定的完美造型;《秋冥》中对少女情态微妙的把握以及作品《桑露》中对光的因素的运用,其中特别对偶然现象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细微的形体关系及色彩的微妙感觉,都源于对偶然现象的敏锐定格的能力。关于瞬间即逝的美的把握是非常难得,没能扑捉到从眼前逝去的美妙场景很是很遗憾。

我的绘画作品追求准确和微妙,强调视觉的发现正源缘于仔细的观察,这种是很累人的。作品《十九秋》光草稿就有几十张,画中树叶几乎每一片都是写生所得,即便如此还留有遗憾。但这幅画对我意义重大,如何呼吸和倒步,何时缓冲和冲刺,我都超仔细的琢磨练习,这是一种练习长跑的技巧,结果无关紧要,我看重的是行事的态度和和过程,用心平而体会彻,所以才做到,静居能化,把所谓“滞气”变成“灵机”。
两条腿走路
近年来看到了一些您的小写意绘画作品,可以说是延续了工笔画的唯美式的意境。
我的绘画经历了从大写意到工笔,又回归于小写意,我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对笔墨的钟情是由来已久的。作为国画家,不懂得笔墨就不懂中国画理、画意与画情,我一直在探索利用传统笔墨规律来表达当代人。写意画和工笔画是两条腿走路,这对画家来说才应该是完整的。若只研究工笔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停滞不前。画写意画一方面有助于工笔画的提高,一方面也有利于对中国画理解与认知。我画写意画除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和中国画的认识之外,也为满足朋友的爱好和需求。
在你的绘画创作历程中,有哪些作品在您看来很重要,如今您还有什么样的新愿望。

《十九秋》、《秋冥》、《苏葡萄》、《丰瑞》等作品,这些作品在我的绘画历程中很重要,每件作品都下了很大功夫,当然也不是全部满意,也有一些遗。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梦想或者说野心也好,就是想画一张巨幅的工笔画,一直还未实现。
石鲁是个天才
作为当代人物画大家,您是如何看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的绘画。
石鲁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做过一个展览,我的老师就带我们去看的。早在文革期间,我就看到过一些石鲁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感觉很新很经典。由于他的绘画实验性很强,也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作品流向市场。那个时候觉得石鲁是一个勇于创新的革新家,对于当时注重传统的画家来说,他被看成那种不顾传统的一类画家,个性较强,显得有些怪诞。他是一个中国梵高式的画家,有一点神经质的感觉,但是他对生活充满了激情,他对自然、对人、对艺术的热爱,感情非常真挚,没有半点虚伪。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很崇敬他,这和他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石鲁是一个说真话不虚伪的很真实的人。他的神经疾病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和他在文革期间受到的打击有大关系。其实我觉得他文革前的状态正是一个艺术家的最佳状态,(艺术家都有点神经质)有点神经质,不过火,恰到好处。一些艺术家杂念与顾虑太多,加之过于理智,冷静,反而会影响其艺术的发展。
石鲁的艺术感觉非常好(不是靠理性的支撑),他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将自然与艺术之间的联想能力非常强,他能将看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一种新的语言,前人没有的语言,他可以创造。比如画家王金岭,他画面用水分的那个胆量,就是从石鲁而来。不是谁都有的。对美的理解,石鲁是个天才,石鲁的绘画所容纳的气质和气象博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石鲁甚至比八大、虚谷还伟大,八大、虚谷的艺术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延续而石鲁的艺术则是一种突破。我认为这个意义重大。
在我看来石鲁的绘画发展经历了写实、写境与大写意的三个阶段。
我认为石鲁绘画的第一个阶段还是处于状物阶段,以写实的观念来对待物象,但不是超写实,是不到位的写实,感情是真挚的,也是那个时代统一的意识,很古朴、气息很正,也很好。石鲁最有价值的就是你所说的“写境”阶段,这个时期艺术创作是很难把握的,要既写实有不完全写实。在绘画上的这种高度提炼、概括、朴拙的美的东西,往往很容易受到真实物象的影响很难画好。有很多人也想创新,但最后组成不了形式。
石鲁他很明画理,对形式特别的敏感。他并不只是对事物的真实表达,而是注重自然事物之间的丰富联想(不直接表现),这恰恰是中国画的思想。石鲁很明白中国画理,每张作品都以高度的概括力,来表现出一种单纯的形式感。我觉的国画家对于形式感的欠缺,这一点也是区别“大家”和“小家”的关键所在。大师往往能把画面组织的单纯、响亮、又有丰富的内涵,小家就会很琐碎,什么都想要。石鲁的作品具有版画的形式,画面黑白灰处理的很好(包括色彩关系)。由于他自身的气质,使得作品很有张力(构图之类)。
我为什么说他对形式感很敏感,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在天津群众艺术馆陈列的一个石鲁作品展,看到他画在小卡片上的作品,数量很多,每一个小构图都很可爱。他能将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变成一个构思,一个画面,这太可贵了,太可爱了,看完以后让我们汗颜。以前,我看过一些石鲁的代表作,包括其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我都很喜欢,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底下的这个功夫。之后我在1981年到山西的黄土高原去写生,我就是以石鲁的这种方式来画草图,直接用毛笔画小稿水墨,很有意思,这就是石鲁对我的影响。
我的老师白庚岩很崇拜石鲁,白老师把石鲁当圣贤一样看,老师在创作中吸取了石鲁绘画中的很多营养,诸如用笔及色墨的表现技法。我的老师特别强调绘画要敢于把笔墨撂在纸上不动,保留住笔墨的精神头,反对在画面上凿来凿去。他说,石鲁就具有光明磊落、掷地有声的精神气概。对于绘画中的线条,他重方而轻圆,重折而不重转,更多的是折笔,注重线条之间气息与趣味。他用长锋泼墨,这样毛笔着力于软纸上就会轻,轻就会厚,硬就会薄,所谓绵里藏针,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人物画家,您怎么看石鲁提出的“山水即人 、人亦山水”的绘画理论与“以神造型”的绘画思想?
一件艺术作品要分三个层次,画山是山,到画山不是山,最后又回归画山是山。状物和物我两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理论上来讲,石鲁的画也是天人合一的翻版,是对画理的高度的认识,也是绘画三种境界的飞跃。他所谓的“山水即人”的理论建树实际上是对实践的总结,前者是理智的,后者则是真真的达到物我两忘。他已经忘掉自然本身的结构的描绘,画山水完全是书写自己胸中意气,他把画山水作为体现自身人格的媒介。画华山就是画自己,画一种真实的自我写照,他完全把山与“我”融为一体了。
关于“以神造型”,我认为画面的神与形是不可分割的,有神必有形,把神放在前面的话,带动形,就算形不准的话也舒服,这两种说法道理是一样的。石鲁提出来的“以神造型”就是说主次的问题,用“形”来促进“神”的形成,在一个则是用“神”来带动“形”的产生。石鲁提出非常高明,神在形具,而且有禅宗意味,(能够给人以联想的语言叫感觉,感觉就是以神先行取得形就有感觉,)最后是希望达到神形兼具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初,您笔下的人物画改变了画坛的流行风气,为中国画坛提供了新的经典样式和别具价值的审美经验,从您的视角看石鲁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拿西方的绘画来比较的话,傅抱石和李可染是印象派,而石鲁就是高更和梵高,起到历史的转换的作用。虽然两者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但是自由的状态,和对艺术的感悟,已经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是一样的。但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的成就比不上石鲁。八大就是纵横气,在文人水墨画上做出了升华。石鲁因为有西画的基础,对色彩的敏感,没有完全选择黑白,尤其对社会和生活的热爱,所以他不会停留在文人画的基础上,而是真诚的表达生活中的美,石鲁在笔墨,形式,色彩上都表现得很充分,难度都要比他们大的多。石鲁积极向上是人生态度很难得,不世俗,不是一味的歌功颂德,这点和梵高很像。这种阳光的心态,是抚平人类心灵创伤的良药,是人类需要的,他会产生和谐之美,从思想境界来说要比他们高的,真诚的情感和齐白石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