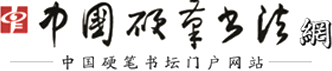周建强:米、王到底能走多远
发表日期:2019-11-19 05:31:25
来源:本站
被阅读[10211]次
1989年某日,《书法报》登载了一篇并不长的文章,却为国内的书家提供了一则有价值的信息,那便是日本人喜欢米芾、王铎的书法。在中国生活久了的文人圈子迅速沸腾起来,海上的沈家集团,南京二不门影响,沙系的普及因熟就俗,一切混乱的思绪便一下给澄清了。
不知是米、王瞬间给人们一种法的提醒,还是传统的再呼唤;还是米芾、王铎技法上的可塑性,抑或是中国人熟知能详伯乐的厉害,想再次体验王学仲、范曾们出口转内销的成功之路。
总之,米芾、王铎之书体风靡天下,无论是书札的普及,还是章草的流行,都不能掩去米、王的权威性。时至世纪末,这两种书体仿佛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样,给统一成一种基准。为此,笔者想就米、王之盛以探讨,并请教于同仁。
一 米芾、王铎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顶峰
米芾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极为张扬的时代,宋代诸皇对书法艺术都是倾注了极大的兴趣。而且高宗、徽宋的书法成就都堪称一代大师。书画家当时的地位也远非今日可比,加之当时的艺术领域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方面都是那样的贫乏。毛笔文化在文人士大夫中是别无选择的,无穷官本位的门面装点,还是艺术本位的创新狂潮,无一不带有功利色彩。再加经过了唐代数百年的法化过程,书法的领域里,一方面受笔正心正论的束缚,一方面受唐代楷、草的惯性影响,宋人的尚意是潜意识中存在的。苏东坡的书法当然没有自己的词赋改革的步子大,只是给书法的情绪化影响、逸笔草草打好注脚。黄庭坚的放射性笔划和他禅意十足的狂草才是书法史上定位的基础。当书法史渐渐由后人书写的时候,也就对他们的职业按照意愿重新进行了分工。这次分工便是宋人在书体上主要承包行书,在崇尚上是以意为主。但宋代的书法家苏、黄、米的重量级别与其他人比较起来,太大悬殊,所以远不比唐代那么星光灿烂,而是廖若晨星。尚意又是极其抽象的事,无论是钟明善的《中国书法史》,还是陈振濂的《尚意书风管窥》,读来都不如唐代书法那么令人对书法家生出更多的崇敬之心。过于高明,需要人们花太多的心事去玩味的意趣,是否会加重今人的心里负担?那么,对于宋代书法的座次,也就是要按需要重新划定一个次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是不是宋人尚意就是目前的“现代书法”,是摒弃“法”,还是发展“法”?那又得回到书体分类上,宋楷除了因人而重书之外,楷书一无可取,“欧、颜、柳、赵”就没有宋人的份。康有为也没有十分肯定宋楷,他只卑唐,似乎连宋楷卑都不卑。与今人谈起书法的入门功夫,即便是十分传统的习书程序,人们也很少能想起宋楷。除开一些投机分子,宋楷是不被人看得起的,这种投机,便是瘦金体。草书是黄庭坚的专利,他是与怀素、张旭成三足之势磨洗之后的中国书法史上的显赫人物。他的行书也承担了一些抽象尚意的义务,但他章法上的避让对书法史的贡献远大于意,这似乎又入了法的范畴。行书这个版块,苏东坡分到了天下第三行书的指标,在一定意义上讲,全面承担了尚意的责任,扛起了一面大旗帜。米芾在做什么?是历史选择了他,他的“臣书刷字,八面出锋,爽利风流,变化万千”,他的“腾挪跳荡,潇洒倜傥”无疑代表了宋的意外之“法”。行书需要兰亭、圣教二序而外,行书还需要另外的“法”。也许“韵”和“意”是行草的精魂,但即便是在苏东坡那里败诉的米颠,也还没有进化到任笔为形,任意涂抹的地步。那么仍有一种天然的束缚。王羲之当年,人们把他的书法改革叫野骛,米芾的刷字却能得到响应,说明了他的实用性。因此,从总体的苏、黄、米行书比较,而不是比较单一人作品,米芾无疑是有宋行书的顶峰。
王铎,在明末清初的书坛上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是忠奸的考验。傅山、黄道周一个在恣肆,一个在飘柔上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今草的功用因有明一代大家的冲击,而带有极大的挑战性。徐渭的目空一切,被傅山承袭了,而且在很大范围内有相通之处,只是一个用长毫圆笔,一个用短毫铺毫。黄道周与傅山有着相似的品格,而且还增加了壮烈的成分。他的书法又在结字上的宽博的方向发展,在无论那一种场合都比较合宜,所以王铎要站住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且从反证的角度去理解王铎的历史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可以肯定地说,收藏、肯定、赞赏一个贰臣的艺术品需要一定胆量和才识,需要寻找一种类似张瑞图书法可以防火的理由一样,当然谁也不会去用火一试他的作品是否创作在石棉纸上。给王铎书法的存留没有找到直接理由,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作品的绝对一流,因为几百年的大浪淘沙,对书画作品的遴选和收鉴者流,也不全由傻瓜和文盲组成。还有一个问题更不客气地说明:明代的草书,大家笔锋不够健,陈道复、文徵明、祝枝山对草书的贡献都不够大。徐渭、八大山人虽然都各有创造,但青藤的破坏是否太大了一点?满幅杀气的作品和满纸的抱怨、不平,在很多场合也许不合时宜,历史已经把把雅玩的书法推上了厅堂。因而从可观、可读、大气磅礴几方面综合评价,王铎又占了上风。加之康乾之际,没有什么大书法家,刘石庵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使命在支撑着,远不及王铎的专业性强,更没有王铎在这方面花费的精力多。之后的训诂影响,有清一百多年整个在重整篆隶的历史了。草书的领域再也没有以前二王家法的纯粹。相比较而言,则是没注意就让王铎领了头功。也许是世无英雄,遂教竖子成名。
二 米芾、王铎代表着旧中国学习书法的程序,是公认的既有传统功力又能出新的典范
米芾的书法是综合二王成功的,他的小楷直取晋人古法,其他楷书因行书所掩,未有极大的影响,李太师收的晋贤十三帖,他却临写得认真,偶尔也写一些篆隶作品,因而从丰富的角度去讲,也实在是个厚积薄发者,如今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小王书作,他都作为做假嫌疑人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屡屡质疑。米芾仅仅活了五十六岁,并不是多寿的艺术家,习书可以长寿的理论对他是个例外,然而就在这56年的生涯,却有了五十几年的刻苦学习阶段,作为一个成名的艺术家,仍然是大字典的编辑,他积古字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五十岁。自云初学颜,后学柳,又学欧褚、段季、魏晋法帖,师宜官、《诅楚》《石鼓文》以及鼎铭等,苏东坡都说米芾书“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其实史载:李北海、沈传师、徐秀海、米芾也好学而不厌。而苏东坡却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就因诗文获罪被贬黄州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早已在三十几岁就名满天下了,作为江西诗派鼻祖的地位,也远不到五十岁这么老;无论是蔡襄还是蔡京,也没有五十岁那么成就书名。而用这么大功夫研习积字的就只有米芾了。虽然他没有种几十亩芭蕉去学怀素,没有几十年不下楼学智永,因为他不是精专的而是广博的,不是独传一种绝学,而是在创造一种程式,他的书法如此,绘画如此。创造米点法的冲动,远比画得好更可贵。他收藏古字画、奇石、名砚挖空心思,留恋山水的痴情,在镇江筑楼不忍离去,是自然之奇、自然之美的崇拜者,以至于爱得发癫。艺痴者技必精,而对于米芾而言,实在可以说是技进乎道了。
在众多五十岁人都守成的时候,米芾却一反常态,丢弃了他的积古字工作,摇身一变成了前卫得可以的改革家,而且改革的步子更大。
王铎和米芾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在改革大潮中独自做一个守旧派,这种守旧是否与赵孟頫当年的守正是为寻找魏晋文人人格自由的向往。象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里描述的那样在感动和自责的矛盾中,寻找另一种寄托呢?不得而知。赵的魏晋追寻,与王的二王承继,与米的再消化,王铎给世人留下了形式各样的大量法帖,从长卷到巨幛,再到自行刻壁可以说是北魏以后的第一人,他也有为天下法的欲望。中国士大夫的书法大多是诗之余,为官之余,政务之余。米芾做了闲差,书法是专业的,王铎做了二臣,虽然官居一品,仍是书法之余才做官,这种刻苦精神是足以天下学书者立起一种典范。那就是“二王”是永久的远古的唯一的导师,其他的丰富只能是支系与变种。
三 米、王的字型结构与笔法能有短期效应
米芾、王铎的书法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的集大成者,直取米王也可以说是一种捷径。米芾笔法沉着痛快,变化倏忽早已产生出一种丰富多彩的面目,取米直习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从魏晋、唐宋其他书家入手更有成就感。米芾、王铎的书法在气势上有先声夺势的壮阔美,米的字内多变,王的倚侧跌宕。特别是首先将浓淡墨引进书法的王铎,真正能体现墨色的丰富性,浓淡、干湿、润燥,孙过庭叙述了那么多,但真正大胆地玩得墨色之妙的第一人却是王铎。王铎还是平静的,远不是张颠、米颠、杨维贞、杨疯子,只有一种平常心,这平常心却有了伟大的壮举。不但是浓淡墨出现在书法里,还将那些大胆的水墨过多渗得一踏糊涂的字好端端地留在字中,更妙的是,人为地将那大墨蛋后边用极枯的笔划调整过来,这种大枯大润的极端化对比组装在他本来就有意摇摆着的行间,镶嵌在重、浊、深厚的章法中,出现在熔金般的笔划间,那种沉着与空灵的对比形成了极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又恰恰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浓烈的、强刺激性的事物,容易被人接受,米芾与王铎的快感与深刻有他直接的效应。
与此同时,行草这种体制在广大的书法爱好群中占有的份额陡增也是重要的原因,谁也不能否认,整个八十年代书法人刚刚苏醒,还未来得深思的时候,早行者就急切地承担起改革者使命,其立论便是这个时代“尚”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要干什么?加之随口都要只争朝夕,使命感过强,便就有了急切,急切就想抄捷径,当代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口号里,有不拘一格“认”人才怪现象,当时的早行者们想到的问题也与全盘西化者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先拿来再改良的方案。拿来什么,唯一的是日本书法,日本书法的拿来便有了经久不衰的流行书风,这种以打烂风格,幅幅不同为目标的流行书风至今仍有极佳的市场。但当他的流行还在最火热的时候,日本人却还中意王铎、米芾,村上三岛甚至于还在日本成立了王铎书会,中国毕竟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地方,王铎、米芾的还是那样的丰富,能写得一手即便是临习之作也很抢眼,卖好。原来流行书风的追风族,继而又有了绕树三匝、唯米、王是两棵梧桐树的感觉。流行书风没有的是范本即便能写出很日本某位书家一样的作品,写出跟中国某位流行书风的领袖如王镛、郭子绪一样的作品也算抄袭,如果能写出一幅与颜、柳、欧,甚或王羲之一样的字也算是小儿科。而如果临习一幅王铎的作品,写成一手丝毫未变的米体,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成为大家名家,这个其实不用请律师问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历来就知道事实胜于雄辩。君不见曹宝麟教授,黄惇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振镰教授,中日交换教授,徐本一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双料委员。写米,具有生杀大权。河南如今有大名者无论男女,写起草书来几人不谙王铎?获奖作品行草书类几近80%以王铎、米芾为母体。所以,赶海的弄潮儿,便知道了米王看涨的行情,
四、米芾、王铎介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尴尬和许多知识分子锁在金笼还是林中自啼的两难心境有着共鸣
中国书法的很多内在的东西仿佛陆游写诗一样,工夫是在诗外的,中国的唐书之盛是与功名有关的,中国的晋韵也与官场的游戏规则没有太大的矛盾,象唐人的酒量与官位无关一样,饮中八仙全是些名士不假,也全是些高官。唐人以书作为取仕的前提,书法成了挤身仕途的敲门砖,诗是见面礼,是本领有外在表现,封建时期的士大夫与大家名家密切相连。如果这联系过于脆弱,比如嫉妒这玩意儿作怪,那大概就会乱套。宋人书法只提苏、黄、米、蔡,这冠军、亚军首当其冲的是受害者。以致于东坡也会说自己被聪明误一生。因何而误,露才。那米芾就比较复杂了,才是高超的,无论诗书画,怎么才能自保,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中,他选择了癫,但他的癫,明显不同于徐渭、杨维桢,颇类宫庭皇嗣们的把戏,以此作为保护,只是为了让妒嫉的人不要过于提防。官本位的中国,几品太重要了。他一不小心就混到一个副部长做做。但并不在官场留恋什么,所以,在皇上面前也敢耍赖不还砚台;跟朋友在一起也敢以死相胁,贪污人家的名帖。不赖不贪的只剩了官,这样的人,官场上还谁跟他过不去?这一点他的癫可以说有点高明,象老子那样,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他纯乎技法改革的思路,使他超然物外,真的有点通脱,还有一点那更重要,便是不结盟。政治上和艺术上都不结盟,所以有不战而胜的奇特效果。因为当时的帝王们特好此事,结盟有时候也是危险的征兆,以至于成了无论是元佑党人,还是蔡氏集团,乃至皇帝、太后,人见人爱,不象东坡那样,虽然也有太后的关照,也未能逃脱很多劫难。米芾也有同样的背景,却用他办了不少的事。
王铎仕清,人称贰臣。仕清又是满人统治,心里总是有大汉民族高高在上感觉的人们眼睁睁就看着几十万满人的马蹄踏到北京城,继而统治了全国。也许是因为中州这个作为中国的象征在历史上太多易主,哪一个民族一旦统治了中国,都要在那里撒野。特别明显的莫过于龙门石窟了,王铎没去过龙门,我不会相信。虽然当时北碑的吹鼓手们还没有吹到脸红脖子粗,但龙门的艺术瑰宝王铎不可能不借鉴。起码他书法中的深刻和棱直方折的部分我看“二王”与米芾是没有那种遗传的印痕的,独创的有可能。但直取龙门也不能排除。作为一个文化人,要让他的骨头太硬实在是难,事实上他后来在清政府的政协也没能力作多少祸族殃民的事,作了一个闲官,高工资买了一些好宣纸,好绢,写了些好字。成名以后的收入刻了些帖,甚或还大胆自负地刻上石崖。从保护遗产的角度去看清政府,也不见得太错得离谱,你一定要他去反清复明,投笔从戎,他不是那块料,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何况大势已去,复了明又能怎样?
如今的艺术家,尽管有人对艺术家的职称关心,但毕竟知道了它与官道的不交叉性,各种展览请官们提个字,剪上彩,装点一些门面,但毕竟不太去把自己的“几品”跟他们挂钩,书法家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相对纯粹化的时期。活跃在书坛上的大家、名家们,其年龄大多在50至70岁之间,他们都经历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对政治上今天你说他是骗子,明天他说你是骗子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十分在意了。米芾那个复杂的大环境没有了,小环境仍在,君不见全国那么多的小圈子,是唯才是圈吗?全国开了一个自什么会,坐在会场上的多半是评委的学生,这种方式颇类日本的学习书道方式。王铎的节变了,他在书法上却是不屈不挠的,那么米、王是否就没想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没有象杜甫那样喊着随当时的舜尧醇一下风俗。一个做副部长的米芾,一个做政协主席的王铎也曾试着在政治上一试身手,没有好手气,便就成了专业人士。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以上年龄组的优异者,其心境与米何其相似。当然艺术上的指鹿为马,和盲目历来就没有人奇怪过。正是因为盲从着大量的票友,书法界才愈见热闹,这就是书法热托长了另一段尾巴的缘故。象帝国主义死不僵一样,书法热是退潮不退水,米、王的发现及从事米王二体领袖们的率先垂范无疑是书法热的又一拥薪炭。而这些领袖们如此恒久的看好米王的行情,难道和锁在金笼与林中自啼的矛盾心境没有关系,如其不然,简淡的弘一呼声那么高,怎么没有从者如流?
五、米、王是行草技法的高峰,无疑也是技法改革的梧梏,谁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所以单靠这些在书坛上位高权重的人也很难支撑,米王肯定是走不了多远
历史上出现了米芾,米体书家曾出不穷。但都纷纷成了过客。无论是米友仁还是吴琚,尽管他们写得比米芾还米芾;王铎却是一份发黄的线装书,升值也是十几年的事,两人都是学习书法必不可少的范本,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作为专业书法家,他们遭遇了太多和当时及古代书家相同的经历,比其他书法多的则是,成名早,社会地位高,作品在社会上的流传量大,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已经是片纸只字,人争相宝之了。他们二人的书法在自己的领域里实在是一种绝活,无论你想以什么样的变法去变革,其结果都是一样,其他熟知米王者,不是看作克隆,便是认定积字,象孙猴子一样,如来佛的手掌心是无论如何也翻不出去的。
元代赵孟頫也直取二王,与米芾的路子很近,他都说“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赵秉文评《多景楼诗》云“钟王之清润,欧虞之简洁,颜柳之端严,诚为鲜俪”。高士奇的诗句有“清雄超妙气凌云”的称赞。但无论如何奇道妙,都与《思陵翰墨志》上说的感受一样“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地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其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米芾的极致使历史上的诸多大师望而却步,他的承继们大多顶礼膜拜者众,可真要为了一句“江山代有才人出”来作注脚,那却实在是难,不否认今人远比古人聪明,更不否认现代印刷术的发达,眼光,眼界都是米芾们不敢想象的事,也同样承认百花齐放的书坛现状,和对百花齐放要求的人们有理由认为米芾及米系书法继续冲撞在传统的大河中,然而这种行业的垄断,一定会带有相应的时效性,过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期而至。所以,米体的流行,应该是到了尽头,到了应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王铎的情况有所不同,人们公开认识王铎来自于新时期将忠奸与字如其人的概念辩证之后。有关王铎熔金般的线条,浓淡墨的首次应用,二王变体之后由小巧娟秀变得大气磅礴。日本的王铎书会和过早透露信息回国的日本人喜欢米王,都为王铎的风行不衰奠定了基础。王铎用他的专业实践几乎将今人的类似于展览、厅堂、寺庙、古迹、景观的所有地方都用过了,甚至于自己为了不朽还刻了摩崖。从方法和推广渠道上讲超越都难,更不用说字法和章法上。
写米王容易写象,因为他们在“法”上的极致,明显的特点使他们永昭书史,难在于变,变的契机的出现,和在认祖以后出新的顿悟。谈及此事,从事米、王制作者,无不头痛,因为大名和位子不是恒久的事,炒作也难使其温度保持恒温,有“胡”的危险。而米王作为一种三角形的固定技法给步其后尘者带来了技法上的绝对桎梏,那么这么评委们离任了,退休了,不红火了,在各种斗争中失利了,这米王不就走到了尽头?
因而,米王只能是技法过关的试题,而不是终生可依的外套,包装留给装潢学习吧。因为他们有廉价的电脑,称誉留给马屁精吧,他们也许等你说几句不公道的话,米、王走红快十年了,该退潮了,他走不了多远。
下一篇:
周建强:我说唐人尚法